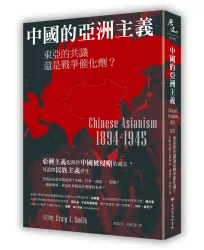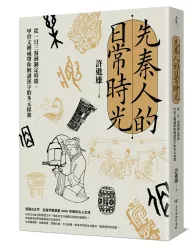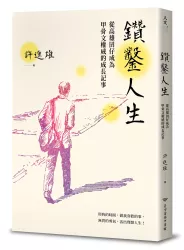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
商品編號:06030130
定價: 400 元
優惠價: 79折 316 元
優惠活動
購買提醒
本商品為出版已久的書,出版已久的書容易產生些許的黃斑、或有些許瑕疵(例如:壓痕、褪色等),不影響內文閱讀。每本書況不盡相同,請考慮評估後再購買結帳,採取隨機出貨。
如想進一步了解書況詳情,可以來信 cptw1897@gmail.com ,或點擊右上角「 客服 」留言詢問,感謝您支持臺灣商務印書館。
內容簡介
全面梳理1920年代婦女運動,
海峽兩岸女權與婦女地位的關鍵研究!
革命尚未成功,「她」們仍須努力。
1920~1930,激烈昂揚卻又埋藏殞滅的十年,
是近代中國由「女權」走向「婦女運動」的重要年代,
即使隔著百年的距離,
「她」——女性,將繼續撼動這個時代
激越時代,女權依附革命積極奮生,大起大落之際留下未竟的遺憾,
中國女權思想,究竟導引一代又一代的「她」走向何方?
歷史記憶隨著時代再一次翻騰,
提醒我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她」來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議各式各樣的「女權」,但無論哪種女權隨後都因迫害,一一宣告幻滅。女界領袖們越來越清楚,如果沒有團體做後盾,單憑知識分子紙上談兵,任何女權都不可能實現。一九二○年,聯省自治運動助長婦女組織團體,跨省域的婦女合作初現端倪。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婦運領袖逐漸嶄露頭角,這是過去五四新文化運動未曾出現的新契機。
一九二○年代,是五四與後五四時期接榫的重要歷史階段,從近代中國婦女史的角度來看,更是「女權」倡議演變為「婦女運動」的重要時期。諸多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的作品,幾乎都一致認為一九二○年代是中國婦女運動聲勢最高漲、席捲範圍最廣的階段。婦運高漲意味著後來的低落,但以往的研究對這中間的起伏多缺乏解釋。
本書內容含括了後五四時期,中國女權、婦女解放從風起雲湧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撥弄的歷史變化過程。
綜觀一九二○年代激進時代的婦運,從後五四時期國共合作始,兩黨隱約有兩條路線之爭。一個走改良、溫和的改革方式;一個走激進道路。不論溫和或激進,一路走來日見個體女權隱沒,集體黨派利益至上的變化軌跡。這樣的婦運,歷經險阻,一路崎嶇。
一九二○年代遭遇「解放」,又迎向「革命」,包括婦女運動在內的群眾運動,大多命運多舛。婦女的主體性在哪?婦運還需要嗎?只有等待激越年代的歷史沉澱之後的反省,才有意義。
作者介紹
柯惠鈴
柯惠鈴
學經歷: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系博士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現職: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著作:《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1920》(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戰時的婚姻與家庭》,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臺北:國史館,2015)。
目錄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第二章 革命初起
第一節 女權爭取的激進化
第二節 婦女的國民會議
第三節 從女工革命到革命女工
第三章 革命高潮
第一節 國民黨婦女部與共產黨婦女協會
第二節 1920年代從廣東到全國的革命婦運
第三節 革命中的兩性及性
第四章 革命幻滅
第一節 訓政階段的婦女協會
第二節 左派女性回憶中的革命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試閱
第一章 緒 論
(一)
許多學者對1920年代的研究,不約而同指出五四及後五四時期,是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中國諸多變化的根本源頭。1920年代的重大變化,如列寧主義式政黨的引進、極端民族主義、以階級觀點重組中國社會、思想界的分化,後來無一不影響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思想各種歷史走向,以迄於今。1920年代的一個代表性現象是「革命」在中國取得至高無上地位,從北到南無人敢公然批評革命所指稱的激烈變革,因為這寄託了中國求存求強的集體心態。從此,「革命」就成了書寫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主要脈絡,不斷革命論實肇始於1920年代。搭配「革命」風潮,就是一黨執政的確立。深重的國家危機,給予政黨強化自身地位,壯大自身力量,並走向一黨執政的機會。政黨為組織起一盤散沙式的中國民眾,他們理直氣壯聲稱必須先鞏固自己的權力,甚至利用各種政治工具、組織方法來控制社會每個階層、每一個領域。
1920年代,儘管有意識型態的差異,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共產黨)助成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的改組,兩黨合作建立了一黨執政的政權統治型態。誠如費約翰教授(John Fitzgerald)說的,一黨執政的政權統治,從1920年代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跨越了近六十年。80年代末,臺灣的國民黨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一黨執政政權統治型態才遭到挑戰,不得不改弦更張或做出些讓步妥協。1920年代在中國政治史上是重要的十年,前此,「自由民國」已然萌芽,但根基未穩,至少到五四時期,許多問題的討論,是極度個人化、多樣化並且沒有明顯的「派別化」。到1920年代初、中期,尤其是1923年左右,階級學說的介入使許多問題討論趨於二元對立。婦女、女權與男女平等,這些在十九世紀末就已大量進入公眾視野的政治社會改革議題,在1920年代從問題本質、解決手段到預期結果也都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20年代前,關於中國女性何去何從,人言言殊,你方唱罷我登場,五四新文化運動堪稱中國女權討論最多元的時期,知識份子、出版界菁英、大學年輕學子,把女權當成社會烏托邦或人生夢想來談。雖然女權問題也背負中國富強的重責大任,但畢竟浪漫謳歌、大膽放恣的成份不在少數,多元、熱鬧繽紛的女權討論在1920年代初期已出現收束的趨勢。
1921年,中共成立,這個新生的黨服膺階級學說的經濟決定論,在他們沒有太大實力的情況下選擇加入國民黨,幫助後者進行國民革命並進而壯大自己。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1924年進行改組。孫中山本意是靠向英、美,不料英、美態度冷淡,當蘇聯向孫中山招手時,雙方可謂一拍即合。蘇聯加上共產黨的影響,國民黨一大後喊出「反帝」、「反軍閥」作為國民革命的主要政治號召。宣傳、組織與訓練伴隨蘇聯式政黨,一併成為新興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時首重的政治工作。具一黨執政雛形的國民黨打著求國家統一、為人民謀福利,順天應人國民革命大旗,毫無二念的把「人民」改編成各個階級,婦女有些怪異又勉強的從「女界」、「女性」變成國民革命的「婦女」,之所以怪異勉強是因為「婦女」無從指向特定的階級,因為想像或實質「婦女」都應是跨階級的集合體。「婦女」既不能指向任何特定階級,註定了階級學說碰到婦女,就只能閃躲或費力自圓其說。「婦女」是國民革命群眾的一個組成,但又缺乏階級明確界線,「婦女」這樣含糊的「群眾集體」,是理解國民革命婦女運動迅起忽落的關鍵,同時,也是後來國、共兩黨分道揚鑣後,各自擇取婦女運動主軸時,日漸清晰而斷難模糊的分野。
與階級觀點同樣重要的是,有關左派、右派與中派的政治劃分「左派」的說法不單單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治鬥爭中的產物,在革命至上的時代條件下,很快的,「左派」日漸與革命激進化劃上等號。左派海納百川,小資產階級也變成左派同路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脈絡下延,剛剛從城市資本經濟與學院知識群體中輪迴脫胎出來的「新女性」,因為作風大膽,也可能是虛榮、淺薄或好逸惡勞,總之身價及聲望大跌,輿論潛藏著對「新女性」的不滿與不屑,時間大概就在1920年代初期。「新女性」一些被公認的負面形象,遭到輿論唾棄,至少現實社會中被認為有「新女性」嫌疑的,或多或少都進行著自我整飭,於是和「新女性」分庭抗禮,更有革命風采的是小資產階級女性站上了革命舞台。「小資產階級女性」是伴隨革命誕生的婦女群體,這個婦女群體若要依據嚴格的條件來辨認,可以說是徒勞,但模糊的要件諸如支持革命、反對守舊、具有反叛精神、自由自主、外表素樸文雅、浪漫勇敢等等,條件可以繼續增加。模糊又清晰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形象,她們伴隨革命的弔詭而存在,正好說明革命與婦女自1920年代牽扯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變化,往後,只要革命再起,無論時空條件的變化如何,「小資產階級女性」總是會一次又一次進入革命的論述,或翻新或擬舊,起始的源頭通通是1920年代。
192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學說進入中國知識界,一種嶄新的運用經濟角度來解釋婦女地位的看法,很快傳播開來,尤其是馬克斯、恩格斯有關家庭私有制與婦女地位低下關聯所提出的看法,在患貧不患不均的中國具有極大的煽動性。1921年中共成立,對於婦女地位經濟決定論,更是傾所有黨員之力運用各種言論載體賣力推銷,國民黨受到婦女問題經濟決定論影響,認定婦女運動是婦女集體起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締造一個強有力政權,然後婦女集體福祉便可以在新政權主持下全部獲得保障。192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國民黨以人民利益代表的立場宣佈對內政綱,其中第12條就是婦女地位經濟決定論變化而來的革命婦運概說,總之,國民黨牢牢掌握婦女全體利益仰賴的是國民黨保障的婦運方針。一大後,國民黨黨中央成立「婦女部」,作為指揮籌劃全國婦女運動的最高領導。同時,「婦女」取得與其他社會階層,包括農民、工人、商人、青年一樣平等的國民地位。婦女部是國民黨黨中央的群眾工作部門,兼有國家政府行政職權。1924年後,廣東境內大小軍事行動,都可見到婦女部組織省內婦女或搖旗助陣或救傷卹亡。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在婦女部組織、宣傳、訓練下逐漸成形的婦女幹部,她們帶領各自的婦女工作隊伍,有紀律、有計劃、講效率,配合國民革命軍事政治行動,成績亮眼。婦女部工作與國民革命相互加乘,彼此信心大增,於是1926年年初,國民黨二大時,再次重申婦女地位的提升與保障,和婦女為革命貢獻是一體兩面,國民革命成功之日,即婦女集體地位自然提升之時。
1920年代的婦女運動,已看到兩個分歧點。經濟決定論致使「無產階級婦女」躍居成為婦女運動中的新要角,女工力量受到重視便是其中顯著現象。除女工外,廣東婦女工作已開始注意到「底層婦女」問題,底層婦女包括的範圍非常廣,對象不明確。就實際人口比例來說,底層婦女確實是婦女中的多數,問題是底層婦女大部分不識字,過著與世隔絕、蒙昩未開的生活,要動員這樣一群婦女並不簡單,革命的婦運卻試圖突破重重難關,組織與訓練「底層婦女」。知識菁英婦女與底層婦女大規模攜手合作,是1920年代婦女運動走出五四新文化女權觀的一大特點。領導婦女工作的女幹部們,她們以底層婦女代言人或輔助者自居,脫離紙上談兵的婦女解放,婦女幹部面對是底層婦女生活的真正現實,兩個婦女階級未必有有共同的語言,在革命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二元劃分中,很不幸的,婦女幹部、知識婦女、菁英婦女相對底層婦女,通通成了「被壓迫者」一員。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暴露不同階層婦女間存在的矛盾與緊張,待國、共分裂後,國民黨由菁英婦女全面掌控婦女工作,群眾只能被「救贖」,不能分享權力,此種格局一直維持到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始終沒有改變。至於共產黨,則奉行群眾婦運路線始終如一,不論是土地革命階段,抗日邊區經濟建設,乃至1949年在中國當家作主後的各類革命,都可見群眾婦運的威力。
1925年,由共產黨女黨員主導的廣東婦女協會組織完成,國民黨婦女部較穩健的婦運路線變成資產階級式,與原來婦女協會注意底層婦女解放的無產階級式婦運方向,形成出兩條路線之爭。因為國民革命大旗的遮掩,使國、共兩黨婦運領袖暫時維持表面合作,等到國民革命軍進抵長江流域各省,國、共兩黨婦運爭執逐漸白熱化到互相難容的地步。1926年,國民政府北遷武漢,左派勢力居上風,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婦運取得主導地位,武漢掀起革命婦運的高潮。激進化婦運壓縮穩健派的活動空間,整個武漢地區陷入女子解放的瘋狂浪潮,拿著剪刀到街上強迫婦女放足、剪髮,時有所聞,寡婦不准守寡,一律改嫁,據傳甚至還強迫分配給男同志。還有結婚、離婚權,男女同樣自由平等,甚至有人公開喊出打倒貞操、自由性交,武漢的婦女解放程度由那些從長江上游逃到下游的人們口中說出,光怪陸離,難辨真假,但過激的婦女解放鐵定令許多人備感威脅,「革命幼稚」現象使所有地方軍人、豪紳、商人等「反革命」勢力通通站到一起,「婦女」沒有武裝,註定在反革命力量發動時會犧牲慘重。
1927年4月,國民黨在南京、上海兩地發動清黨,宣告與共產黨的政治決裂,一場黨的屠戮爭權就此拉開序幕,武漢在汪精衛主導下,不久也奉行清黨分共。共產黨組織瓦解,黨員星散,不是改換身份就是隱沒地下。武漢婦女解放在分共風聲鶴唳情況下,迅速消聲匿跡。保守的地方軍事實力派與豪紳聯手,給予激進婦女運動深重打擊,許多聳人聽聞的對婦女羞辱性的殘虐迫害手法陸續傳出,青年女同志人人自危,暴力反撲使革命的婦女解放染上血腥。暴力反撲下,「革命」、「解放」等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歷史,填塞了更多黨派糾葛、複雜人格魅力與作風評價。
隨著武漢的婦女解放風消雲散,1927年年底,國民革命大致已完成底定中國的軍事任務。緊接著,廣大群眾何去何從的問題,迫在眉睫。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正式宣告群眾運動走入歷史,婦女部和其他各部同時撤銷。軍政階段既已結束,婦女工作相應就要有新方向。在軍政過渡到訓政的這段時期,國民黨著手進行黨務整理,工作重點放在清理各地不同的群眾運動。1928年,黨務整理時期,大部分的群眾組織都被取消,只有婦女因始終位在群眾運動的邊緣,於整理時期反得到組織復甦的機會。這時沒有國、共政治矛盾與紛擾,整理黨務時期各地婦女工作負責人便較能齊心協力,儘管不是邁著群眾動員那樣激情昂揚的步伐,婦女工作走向更加細水長流的從婦女教育與職業技能培養,這是後來國民黨婦女工作的基本走向,1920年代眾聲喧嘩的熱鬧、跳上竄下的群眾婦運,似乎從此一去不復返。
推薦序文
一九八○至九○年代間,臺灣婦女與性別研究正方興未艾。美國女性主義學者的理論著作,以及西方有關中國婦女歷史的學術研究,如Kate Milllett、Margery Wolf、Emily Honig、Judith Stacey、Elisabeth Croll、Kay Ann Johnson等人的專著,在我知識欲望的渴求下貪嚼狂嚥,幾乎通通讀完。此後一頭栽進近代中國婦女與性別研究,以迄於今。現在回頭看看這些對我具有震聾發聵影響力的學術作品,多半是以「左派」觀點來看待中國革命與婦女解放,他們所關注的是社會主義與中國女權究竟能否攜手並進。隨著二十世紀遠去,一九八○至九○年代的議題不僅重要性沒有消減,反更見其為引導研究二十世紀關於近代中國女權與婦女運動一個重要的線索。
在逐步增加的研究與閱讀中,關於近代中國女權與婦女解放在歷史轉變中的「延續」與「斷裂」問題,漸漸深植在我的腦海中,特別是關於近代中國的婚姻、家庭變遷研究,隱然都觸碰這個問題。回想最初在摸索近代中國女權與性別研究的門徑時,我已懵懂地認為「延續」與「斷裂」,在近代中國婦女歷史研究中有獨特的轉變脈絡可尋。所以,追尋歷史中的婦女運動圖像,不但須聯繫近代中國歷史的其他研究領域,同時還要構築婦女與性別研究自身的歷史解釋。
屬於我個人研究經歷的「延續」與「斷裂」,也有跡可尋。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與友人特意前往臺北凱達格蘭大道前,貼近觀察由「下一代幸福聯盟」主辦的群眾集會,藉以深入瞭解在臺灣已經熱議沸騰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議題。這次親臨其境的訪查,走入群眾中,不久手上就多了張「公民意見連署書」,標題寫著「婚姻家庭,全民決定,子女教育,父母決定」,或許是為了凸顯反同性婚姻合法議題,這個標題簡潔有力,但我當下卻不能馬上明白這四句話該如何解讀?我把這份資料當成「歷史資料」,鄭重留了下來。這次的集會、文宣標題釋放時代遽烈變革的矛盾訊息,而我卻不由自主跌進歷史深邃幽遠的莫測變化中。我一再對身旁友人說,你知道嗎?他們所談的,要修改的那部界定婚姻制度的《民法》,是國民政府一九三○年在南京公布的,這部民法有繼承五四婚姻觀也有當時德國﹑日本一夫一妻制精神的模仿。《民法》的歷史性與當下贊成同婚與反對同婚,看起來似乎沒有太密切的關係,事實上,對我一個始終對近代中國婦女與性別研究有濃厚興趣的人來說,卻是一幕幕歷史變動中,婦女運動及女權起起落落的真實歷史場景。
上個世紀的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中國婦女在廣東迎接第一個「三八婦女節」,自此這個由國民革命運動介紹給婦女的節日,成為中國婦女與國際接軌,宣示性別權利與號召團結的特定紀念日。三月八日,算是全球性的婦女節,各國婦女在當日的慶祝活動,有時會跨越國族、跨過階級,有些地區則始終難逃政治的擺弄。近代中國歷史反覆印證,婦女運動及女權若離開政治,往往就會迅速消褪,乏人問津,國家、法律向來是女權提升中可靠的支柱,這就是為什麼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到二十一世紀臺灣,女權和婦女運動與革命、政治牽連如此之深。女權議題,真的都是為婦女嗎?在與政治合作時,婦女的利益是否也被出賣了?或者政治永遠擺脫不了權力的操弄,婦女的權利不過是塗抹政治面目的胭脂?
二十一世紀臺灣的婚姻權議題,與上個世紀三八婦女節進入中國的兩個情節有了呼應,觸動了我重新回頭整理這十年來,陸續寫出有關中國一九二○年代婦女與革命的研究成果。一九二○年代距今已近百年,那是中國從五四走向以黨治國,最關鍵的十年,當年國、共兩黨對於婦女運動及女權都有明確的主張與想法。後來,兩黨分家,再後來,兩黨各自建立政權,並治理國政,在婦女政策及女權保護上也走出不同的道路。十年以前,我的學位論文就曾經注意一九二○年代國、共婦女運動的合與分,同時,還有兩篇文章寫到訓政及左派革命女性問題。不過,當時缺乏對二十世紀一個通貫性的理解。十年過去了,不論是近代史研究或是當代臺灣女權的進展,都給我新的啟發、視野與研究視角,對於一九二○年代的婦女與性別做出了完全不同於十年前的詮釋,而這個看法,自信的說,當然更加成熟。
十年走來,在近代中國婦女與性別史研究上,又跨入抗戰時期。戰爭與性別,其歷史圖景又與革命、政治與性別,不盡相同。研究戰爭中婦女的掙扎、生存於國族愛國聲浪中的裂罅,當然有助於我重新釐清、認識一九二○年代的婦女運動與女權問題的本質,畢竟,歷史臍帶難於割裂,而我也產生了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三部曲的想法。二○○五年拙作,《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一九○○ s—一九二○ s)》,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今年二○一八年,《她來了: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一九二○—一九三○》,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三部曲中已完成二部。第三部,戰爭中大後方的婦女社會群像,正在醞釀中。
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我的近代中國婦女研究的第二部曲,也算是個人在學術歷程中一個小小的里程碑。要感謝的人好多,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對我的敦促與鼓勵,書寫過程中的種種困難,在他們的打氣下,一一克服,同時他們也分享我思考後的興奮與收獲。此外,輔仁大學歷史系的林桶法教授,大力催生本書的出版,他是我在政治大學讀碩、博士班的學長,在學術道路上照扶提攜,令我感念。美國紐約大學的柯瑞佳(Rebecca Karl)教授,是一位灑脫、走在時代前端的女性,她的書、她的想法,引領也啟發了我一些獨特的思考。還有許多的師長,游鑑明教授、羅久蓉教授,研究上成績斐然,是對我愛護有加的老師。在同一領域研究行伍中的好友,如連玲玲教授,我們曾共同合作,努力推動婦女與性別研究在臺灣繼續扎根。重慶大學的張瑾教授,對查閱檔案的遠方女子照拂有加,深情厚意銘刻於心。此外,母校政大的李素瓊助教、蕭淑慧助理,她們對我的書,在校對上花了許多功夫,還有好友高純淑教授及學弟陳佑慎博士鼎力相助,他們幫我檢閱書中文字,可謂鉅細靡遺,這是繁瑣又累人的工作,我對他們心存感激也就不言可喻。最後要感謝的是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幾位朋友,其中徐平先生對我的專書出版,不憚其煩地溝通、聯繫,總編輯李進文先生悉心閱後的建議,全都點滴在心。
個人的研究總是跌跌撞撞,有時「柳暗」,忽的又「花明」,一路走來,實不知前方將會碰見什麼。最近一趟四川行,在四川省檔案館裏蒐集有關抗戰四川婦女會的資料,偶然間,一個受訓並被派往四川省某縣視察的女性名字,躍入眼簾,她是呂曉道,一九二○年代南京婦女部的一位知名職員,同時也是國民黨女黨員。四○年代,她成了眾多視察地方政治的男士中,獨一無二的顯眼女性,一九五○年代後在臺灣任國民黨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執行委員,在臺灣的婦運經驗承續自大陸時期。與呂曉道同樣崛起於一九二○年代,活躍又備受矚目的是左派女性胡蘭畦,抗戰期間,她是第三黨。進入一九五○年代,在社會主義政權塑造新時代婦女身分時,卻受盡折磨與拷問。呂曉道與胡蘭畦對照,近代中國女權的曲折歷史,一覽無遺,令人唏噓。近代中國的時代變動,牽引著婦女與性別的跌宕起落,強烈吸引我且又常使我驚悚不已。這是我決定著手梳理上個世紀從晚清到抗戰中國女權發展軌跡的最主要動機。這第二部曲對我來說,是自己性別史研究的承先工作,更是惕勵自己的啟後事業,最近的未來,我一定得接著完成我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第三部曲」。
柯惠鈴 誌
二○一八年六月一日
NT$316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