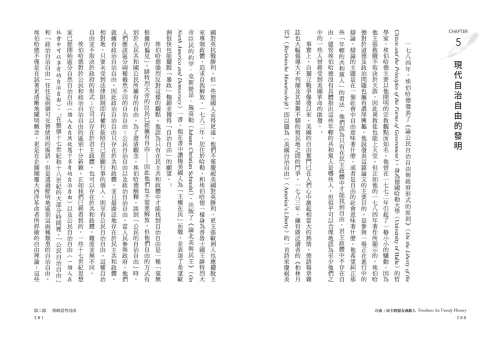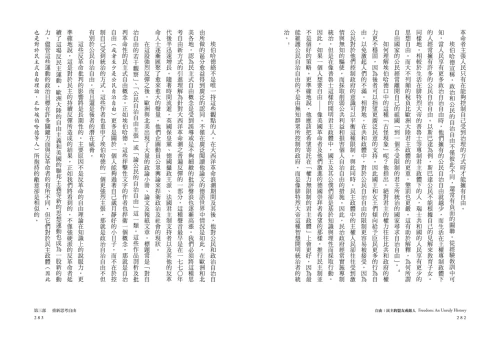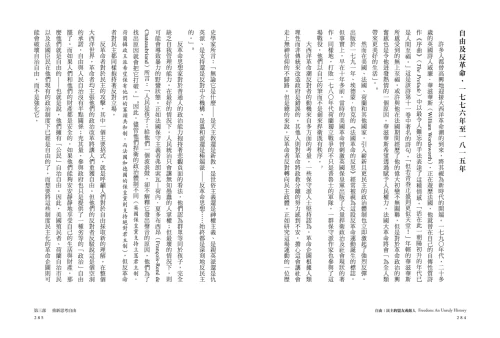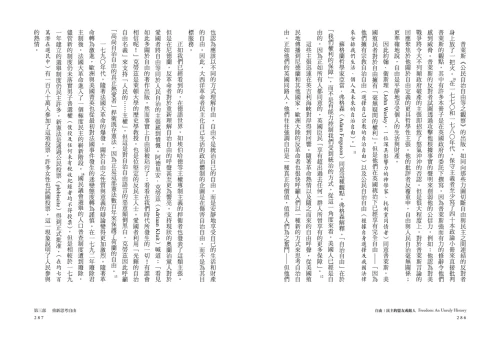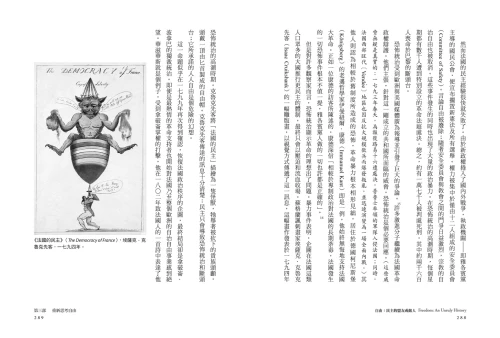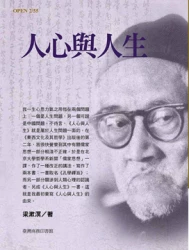內容簡介
2021美國出版者協會PROSE哲學獎得主 全球學者.各大外媒一致好評
「精雕細琢引人入勝」「充滿雄心壯志」「大膽顛覆標準敘事」「迫切而深具說服力」
疫情時代政府強制戴口罩、實名制,侵犯自由的質疑聲不斷;
社會貧富差距與日俱增,追求自由似乎必然伴隨著犧牲平等?
從希臘城邦、法國大革命到極端政治的現代。
自由與民主業已分崩離析,究竟如何解決這個困境?
唯有追尋自由歷史的系譜,才能獲得解答!
在當代社會,自由被視為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權利,每個人都應有不可侵犯的個人領域,行使自身的意志,不被國家政府所拘束。可是,自由的定義並非始終如一,甚至我們現在熟悉的自由,是十九、二十世紀才重新發明的產物。
從古代希臘城邦開始,自由一直都代表著人民自我治理的權利,能夠建立屬於自己的政府,換言之是一種「民主式」的自由。到了近代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的支持者,都一再強調要由人民組織政府、參與政府的決策。美國政治家派屈克・亨利就曾發表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寧死」,表達支持民主自由的強烈決心。
可是,反對革命的分子卻認為,民主並沒有帶來所有人的自由,而是帶來多數人的暴政,才會造成後來法國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恐怖統治,因此他們提出嶄新的自由概念,認為應該限縮政府的權力,讓人們享有個人自主生活、生命財產的領域。這不僅是我們現代所熟悉的自由定義的誕生,更是自由與民主分道揚鑣的開始。
此後,「自由」成為眾人爭論不休的話題,左派、右派、民主、專制的支持者都宣稱他們是自由的捍衛者,至今都是眾人爭論不休的焦點。二十世紀初的共產主義者認為,為了獲得真正的自由,讓人民擺脫被資本家奴役的困境,必須進一步解放經濟上的不平等。但諷刺的是,這樣的理解最終卻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後來墨索里尼、希特勒納粹政權的誕生。
因此,「在一個社會中,或者是作為一個社會,人如何獲得自由?」,正是本書要解答的課題,將審視兩千多年以來,在一般所稱的西方,如何去思考與討論政治上的自由。這段故事一路上會探究諸如柏拉圖、西塞羅、馬基維利、洛克與盧梭,以及當代的弗雷德里希・海耶克、以撒・柏林及漢娜・鄂蘭等大名鼎鼎人物的思想,也觸及到那些政治思想上相對不為人知的人物,像是十九世紀編寫韋伯字典的諾亞・韋伯斯特,他就是第一個用美式英語來定義出「自由」(liberty)的人。在這段探索自由的漫長歷史中,我們尤其應該記住,對我們現代民主制度的締造者而言,自由、民主及平等之間並不存在緊張關係,始終是相互交織的。唯有釐清自由概念的演進過程,才能回到當代社會,捍衛生而為人的基本價值。
作者介紹
安娜琳.德黛
安娜琳.德黛Annelien de Dijn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現代政治史教授。她的研究聚焦在17世紀至今的歐洲與美國政治思想史,並略有涉獵古代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著有《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的法國政治思想》(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from Montesquieu to Tocqueville)。
譯者簡介
陳雅馨
陳雅馨
臺大社會所畢業,清大社會所博士班修業畢,自由譯者,單獨譯有《大腦與意識的知覺》、《路西法效應》、《聖經的教養智慧》、《重播》、《失控》、《正義與差異政治》等書。
名人推薦
(依姓氏筆畫排列)
專文導讀
陳禹仲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葉 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好評推薦
朱家安 哲學作家
顏擇雅 作家
「自由的實踐不僅在於落實古典自由的人民主權,因為落實人民主權、卻未能擁有充分平等的政治,將會成為一個少數菁英擔憂資源重新分配,進而挪用現代自由概念以限縮人民主權的政治;而這也正是我們現有的政治。而正如德黛所說,也許擺脫如此困境的方式,唯有在現代政治裡,重申自由、人民主權、與平等這近乎三位一體的觀念集結。」
──陳禹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在一個少有人願意為民族的解放而犧牲,職業與愛情或許是人生最偉大的抉擇之民主時代之中,這樣一本企圖帶領人們重溫歷史更加淵遠流長的另一種自由,無疑是思想史之外更重要之意義。或許也是作者的真正書寫意圖。」
──葉 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雄心勃勃,令人印象深刻……探討了從古代世界、革命時代到冷戰時期,自由概念的另一段歷史,描繪了當今的自由概念──如不受政府監督或壓迫的自由──偏離其更經典和由來已久的自治定義的時刻……正值自由和民主的危急存亡之秋,像這樣的書比以往更為重要,因為我們的社會正在思考過去的遺產和未來的展望。」
──《國家》雜誌(The Nation)
「一部精雕細琢、引人入勝、與我們時代密切相關的歷史。」
──《科克斯書評》星級評價(Kirkus, starred review)
「發人深省……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右派和左派的支持者,都聲稱自己是自治自由(Liberty)的保護者,卻對其意義抱持著截然不同的理解……這本深入解析的思想史擁有遏止政治兩極化的潛力。」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本書大膽且充滿雄心壯志,將對我們如何思考自由在西方傳統中的地位,產生巨大的影響。」
──薩繆爾.莫恩(Samuel Moyn),《不足:不平等世界中的人類權利》(Not Enough: Human Rights in an Unequal World)作者
「這本書既具權威,又相當精緻,是一部規模宏大的歷史。德黛成功以清晰和輕盈的筆觸,將過去的重量帶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自由及其脆弱性上。」
──達林.麥克馬洪(Darrin M. McMahon),《神之怒:一段天才的歷史》(Divine Fury: A History of Genius)
「德黛以非凡的廣度和博學,敘述了西方關於思考自由的全史。在這個過程中,她還深刻地顛覆了標準的自由主義敘事,使我們相信,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自由──即獨自做自己事情的機會──是最近才發明的。對於歷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所有喜歡偉大思想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
──索菲亞.羅森費爾德(Sophia Rosenfeld),《民主與真相:一段簡明的歷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
「德黛寫了一本驚人巨著,探討自由的歷史及其多樣的意涵。這本書討論的範圍廣闊、文筆優雅、有著驚人原創的洞察力。在未來的許多年裡,我們都將持續閱讀這本書。」
──麥克.祖克特(Michael P. Zuckert),《啟動自由主義》(Launching Liberalism)
「兩千年來,自由都被認為是民眾自治。但十九世紀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將自由重新定義為針對國家權力的個人權利保障,而民主式的平等則是對自由的威脅。這本適時的書提出了迫切且深具說服力的論述,在這個不平等與日俱增的年代,重新思考自由與民主。」
──席普.斯圖曼(Siep Stuurman),《人文的發明:世界歷史中的平等與文化差異》(The Invention of Humanity: Equal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World History)
「本書為西方傳統中自由的定義,這個龐大而混雜的主題賦予驚人的清晰度。關於抵制民主的嶄新見解和措辭犀利的結論,讓任何對我們當前困境的源頭感興趣的人,都必須閱讀這本書。」
──琳.杭特(Lynn Hunt),《歷史學為什麼重要?》(History: Why It Matters)
「一本精彩的書,寫得非常好、引人入勝,且令人信服。德黛提供了一個關於跨越兩千年的自由概念的全面歷史,認為像我們今天這樣將自由與有限政府連結起來,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概念。」
海蓮娜.羅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自由主義的失落歷史》(The Lost History of Liberalism)
目錄
導讀 「自由」的系譜 陳禹仲/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導讀 歷史作為自由與民主的雙重變奏曲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引言 一個捉摸不定的概念
第一部 自由的漫漫長史
第一章 不做別人的奴隸──古希臘的自由
第二章 羅馬自治自由的興衰
第二部 自由的復興
第三章 自由的文藝復興
第四章 大西洋革命浪潮中的自由
第三部 重新思考自由
第五章 現代自治自由的發明
第六章 現代自治自由的勝利
結語 二十一世紀的自由
謝辭
圖片來源
註釋
試閱
第一章 不做別人的奴隸──古希臘的自由
西元前四八○年,有兩名斯巴達年輕人,分別叫作斯帕蒂雅斯(Sperthias)和布利斯(Bulis),他們從家鄉出發,前往波斯的首都蘇薩(Susa),肩負著一項十分危險的任務。數年前,波斯王大流士(Darius)派遣使節前往所有的希臘城市,要求他們奉上「土地和水」作為貢品,即要求他們象徵性地承認臣服於他的權力之下。大流士的要求令希臘人群情激憤,斯巴達人將這些不幸的信使扔進了深井裡,跟他們說,去那裡拿你們的土地和水吧。他們這樣做不僅大大得罪了大流士,還得罪了諸神,因為使節被認為受到神的保護。猶豫再三後,斯巴達人決定派遣自己的兩名使節,前往蘇薩向大流士賠罪。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自願接下這個任務,他們很清楚,波斯王極可能讓他們嘗嘗自己種下的苦果。
這兩名年輕人在執行其危險任務時,表現出驚人的無畏精神──甚至可說是魯莽。前往蘇薩的路上,他們在波斯將軍海達爾尼斯(Hydarnes)的宮殿中暫時停留了幾天,海達爾尼斯是愛奧尼亞(Ionia)的總督。海達爾尼斯十分熱忱地款待了他們,除了將其奉為上賓之外,還舉辦了一場華麗的宴會來歡迎他們。當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正大快朵頤,話頭轉向了斯巴達與波斯間的關係,這段關係正陷入前所未有的陰霾之中。就在要求希臘人奉上土地和水之後不久,大流士在馬拉松(Marathon)被雅典人和普拉提亞人(Plataean)的聯軍打敗。但波斯人繼續作著征服霸業的美夢,十年過去了,現在大流士的兒子薛西斯(Xerxes)正在集結一支大軍,準備前往征服斯巴達和其他桀驁不馴的希臘城市。
海達爾尼斯試著勸說他的客人,斯巴達人還是以主動臣服於薛西斯為上策,不要坐等失敗的苦果。海達爾尼斯說,如果他們把自己交到國王手裡,將會得到很好的待遇。事實上,如果他們為薛西斯忠心效命,只要國王一聲令下,他們和他們的同胞甚至可能成為全希臘的統治者,但如果他們繼續頑抗,一旦戰敗,可別期望得到任何憐憫。而薛西斯肯定會贏得這場戰爭,因為無論從武器或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波斯大軍的實力都遠勝於分裂的希臘人所能集結起來的兵力。
這個建議也許是出於一番好意,但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可聽不進去。海達爾尼斯知道當奴隸是什麼滋味,兩人粗魯地回答,但他顯然一點也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是何等甜美,否則他就不會建議他們放棄自由,來為波斯王服務了。一個自由人永遠不會同意被另一個人統治,他將捍衛自身的自治自由,有必要時,就算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歷史沒有記載海達爾尼斯對這番慷慨激昂的陳詞如何回覆,但可以想見整個宴會廳的氣氛瞬間變得冷颼颼。
冥頑不靈的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繼續前往蘇薩去拜見薛西斯。當他們在護衛陪同下一路進到正殿,內心一定感到無比害怕。他們的家鄉斯巴達是個偏僻的小地方,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建築物,但波斯大王的宮殿可不是這樣,這棟建築物就是為了盡可能激發人們心中的敬畏而設計。賓客從大門進入時,可以感受到這是座貨真價實的宮殿,十五公尺高的城牆令所有進入的人覺得自己渺小無比;接著,他們會穿越通往皇宮的巨大廣場,一直往前走才會抵達龐大的正殿。那裡,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看見薛西斯坐在一個巨型石椅上,身旁圍繞著武裝的侍衛和隨從。
但這兩個年輕的斯巴達人沒有因此卻步。當薛西斯的侍衛命令他們俯伏在國王面前時──這是傳統宮廷儀式之一──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拒絕了。即使侍衛將他們的頭朝下用力推到地上,他們仍大聲宣告,不會俯伏在另一個人面前,因為「這不是希臘人的做法」。他們是在玩命啊,薛西斯本有權利因他們的傲慢無禮而處死他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活下來講述了這個故事。他們大膽的言詞逗樂了薛西斯,他並不覺得受辱,反而接受了斯巴達人苛待他使節一事的道歉。回到了斯巴達後,這兩人成了略有名氣的人物。關於他們的勇敢事蹟在希臘世界不斷流傳,最後傳到了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耳裡,他在《歷史》(Histories)一書中給了兩人一個重要的位置。
正如希羅多德轉述的那樣,這些軼聞要傳達的訊息十分清楚:自由對希臘人而言,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性。的確,正如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表明的,希臘人珍視自由更甚於社交禮節──甚至更甚於他們的性命。這使得他們有別於波斯人,波斯人不但受到像薛西斯這樣的專制統治者奴役,而且似乎能平靜地接受臣服於人的命運。希羅多德絕不是唯一提出這樣觀點的希臘作家。「希臘是自由之地」的想法是個經常被重複的老生常談,如亞里斯多德就曾在希羅多德之後約一個世紀,寫下這樣的評論:希臘人(亞里斯多德稱他們為「海倫人」〔Hellenes〕)跟波斯人最大的不同是,希臘人是「自由的」,但波斯人卻是「受人統治和奴役的」。
相較於具有「奴性」的波斯人,古希臘人驕傲地將自己形容為「自由的」,這讓他們對自由的歷史作出了關鍵貢獻。當然,他們絕不是第一群將自由作為奴役的對立面來談論的人。所有近東社會都相當熟悉這個區別。美索不達米亞的語言,如阿卡德語(Akkadian)和蘇美語(Sumerian),都有表達「自由」的詞彙,分別是andurarum和amargi,就像在古希臘語中一樣,這些詞彙要表達的是個人為奴狀態(personal bondage)的相反。事實上,我們已經在西元前三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文獻中,找到提到「自由」作為合法蓄奴或為奴狀態的反面說法。我們的資料來源清楚表明,免於為奴的自由是受到珍視的狀態。例如:在西元前二三五○年,蘇美王烏魯卡基那(Urukagina)就在其統治時期的一段官方歷史中誇耀,已經將他的臣民從為奴抵債的制度中「解放」(free)了。
自由在這個字(從為奴狀態中解放)的意義上,甚至在希伯來文化中佔據著更重要的角色。可能可以追溯至西元前六世紀〈出埃及記〉(Exodus)(雖然裡面所描述的那些事件,應該發生在許多個世紀以前),其述說了猶太人在埃及法老強加給他們的「奴役」之下,是如何地「哀痛呻吟」。猶太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在埃及定居,並逐漸興旺,但他們不斷增加的人口令埃及當局感到害怕,擔心一旦發生戰爭,猶太人可能會站在敵人那一邊。為了擊垮猶太人的精神,法老命令他們從事各種苦役。當猶太人的為奴狀態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他們便呼求上帝的幫助,上帝就透過摩西的協助,將其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後,猶太人就在逾越節(Passover)慶祝他們從「為奴之家」(the house of bondage,他們對在埃及服侍法老那段時間的稱呼)解放,這個一年一度的儀式包括食用象徵著嚴酷奴役的苦澀藥草。
但是蘇美人和希伯來人的文本中慶祝的自由,是從個人為奴狀態中解放出來的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猶太人所謂的拯救,不是被描述為從異族支配中解放出來,而是從受到法老的奴役,轉為服侍神。〈利未記〉二十五章五十五節(Leviticus 25:55)將這點說明得很清楚:「因為以色列子民都是我的僕人;他們是我的僕人,是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必須被理解為合法奴役,而不是異族暴君的政治壓迫,這一點也在〈申命記〉(Deuteronomy)中得到了證實,神命令猶太人每七年就要釋放他們家庭的奴隸,以慶祝他們從埃及被拯救出來。只有在以色列人與希臘羅馬文明接觸後寫成的〈馬加比書〉(Maccabees)中,人們才用政治意義上的「自由」一詞來描述猶大(Judea)一地從希臘化的西流基帝國(Seleucid Empire)中解放一事。
簡言之,在希臘人之前,似乎沒有人用過「自由」和「奴隸」這樣的詞彙來描述和評價政府的類型,然而希臘的思想家們顯然這麼做了。當斯帕蒂雅斯和布利斯宣稱自己是「自由的」,並控訴他們的東道主海達爾尼斯是個「奴隸」時,他們的意思不是說海達爾尼斯處在為奴狀態,畢竟他們的東道主可是個備受敬重、有權有勢的貴族,還是羅馬軍團的指揮官。但是在他的希臘客人眼中,海達爾尼斯卻是個「奴隸」,因為他是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國王的臣民,然而他們身為一個希臘城邦的成員,卻能夠自己管理自己。就這個意義而言,可以說這些希臘人發明了政治自由的概念。他們率先認為自由是具政治價值的,也就是認為自由是一種人們只有在某些政府類型中才可以享有、在其他政府類型中卻不能享有的狀態。但他們並不是最後一群這麼想的人。今天,我們仍認為必須要有特定的政治制度才能維護自由,也仍認為區分自由與不自由的國家是可能的。因此,希臘詩人與哲學家站在一個長篇故事的開頭,這個故事帶領著我們走向今日。
然而,重要的是要理解:古希臘人並沒有發明我們的自由概念。當他們說自己是自由的,他們的意思不是說他們生活在一個有限政府下,或是他們擁有權利法案、成文憲法或權力分立這類的制度。他們的意思是,不同於波斯國王的臣民,他們不受其他人的統治,而是自己管理自己。換言之,他們擁有的是一種民主式的自由概念:在他們看來,一個自由的國家是人民能控制它的治理方式的國家;它不是一個盡可能限制政府干預的國家。
接下來,我們將通過古典時代的希臘,追溯這段民主式自由概念的歷史。我們將考察從何時起、在何種條件下,希臘人開始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以及他們如何開始珍視自由,視之為一種重要的、政治上的善。像希羅多德這樣的希臘思想家不但發明了一種特殊的自由定義,他們還是第一批條理清晰地陳述為何自由的生活值得人們為之奮鬥的人,但這種對於自由的狂熱信仰也在希臘受到了激烈的質疑。到了西元前五世紀末和四世紀,希臘思想中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暗流,這股暗流最終引導著某些最具影響力的希臘思想家拒絕了自由的價值。
推薦序文
一個捉摸不定的概念
今日,大多數人往往將自由與擁有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劃上等號,這些個人權利界定了政府不可侵犯的私領域。但情況始終如此嗎?這個定義使得自由取決於國家權力的限制,但它真的是唯一、甚至是最自然的思考方式,只有透過它,我們才能思考在一個社會中,或者是作為一個社會,自由到底意味著什麼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又是如何改變了對自由的理解?原因為何?
以上便是本書所要回答的問題。透過研究兩千多年來傳統西方世界的人們如何思考及談論政治自由,本書將提出自己的答案。論述將從發明自由的古希臘開始,直至現今。一路上,我探索了一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如柏拉圖(Plato)、西塞羅(Cicero)、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尚‧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的觀點。而這個論述中也出現對政治思想的貢獻不是那麼知名的人物,如十九世紀的辭典編纂家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是首先在美式英語中提供自治自由定義的人。(譯按:關於freedom與liberty的區別,在中英文世界中有許多討論,譯者不涉入細緻的詞義探討,僅以自治自由〔liberty〕與自由〔freedom〕的區別方式令讀者有所辨別,俾使讀者可「自行」、「自主」地透過上下文「自由」地推敲、理解作者對這兩個字的使用,以及其在更廣大背景中如何被認知。此一區別方式放在全書的脈絡中將更顯得有其必要。)
調查的結果令人震驚。我們應將現今對自由的概念理解為一場蓄意而戲劇性的決裂,此一決裂使得我們與某些長期確立來思考自由的方式分道揚鑣。許多個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及政治行動者始終認為自由不是國家對個人的放任不管,而是能夠控制個人受到統治的方式。他們對自由的看法是一種民主式自由概念:一個自由的國家是人民自我統治的國家,即使這個國家缺乏權利法案、獨立的司法制度,以及其他監督正當國家權力邊界的機制。這種民主式自由概念由古時的希臘和羅馬人發展出來,並在現代由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及其門徒加以復興,如尼可洛・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艾蒂安・拉波哀西(Etienne de La Boétie)以及阿爾傑農・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等人。正如著有《政府論》(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十七世紀英國作者西德尼所言,只有當一群人受到「自己制定的法律」統治時,才可能是自由的。
這些人文主義思想回過頭來又啟發了十八世紀末,美國、荷蘭、波蘭和法國的革命者。當這些革命者造反時,他們是以自由為名造反的,但他們所爭取的自由卻不是安靜地享受他們的生活和財產的自由,而是用古希臘和羅馬人的方式來治理自己的自由。一七七四年第一次大陸會議(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所陳述的「所有自由政府」的基礎,是「人民有權參與他們的立法會議」。在大西洋的另一邊也聽到了同樣的聲音,一位傑出的荷蘭愛國革命參與者彼得・弗里德(Pieter Vreede)曾於一七八三年寫道:「如果你不能治理你自己、你的財產和你的幸福,就不能說你是自由的。」
視覺表現描繪了這個歷史悠久的民主式自治自由概念的非凡生命力,所謂「自治自由帽」(cap of liberty,譯按:以下簡稱自由帽)的歷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古羅馬,獲得自由的奴隸會在他們的解放儀式上得到一頂圓錐形帽子,隨著時間推移,自由帽變成了政治意義上的自由象徵,例如:在慶祝羅馬採行祕密投票制度而發行的錢幣上,就出現了自由帽的身影。十多個世紀以後,一七六○及一七七○年代,紐約的叛客們豎起了一根根裝飾著自由帽的自由桿,以此來宣示他們對英國統治的不屑一顧。一七九○年代,這個符號又成了法國革命者日常裝束的一部分,他們戴著紅色羊毛帽來表達他們對自治自由的執著熱愛。
於是,兩千多年來,自由一直被等同於人民自治(popular self-government)。我將在接下來的篇章中詳細介紹這段漫長歷史。一直要到十九、二十世紀,歐洲和美國的政治思想家才開始傳播思考自治自由的不同方式,許多人開始主張,自由不是誰在治理的問題,相反地,自由取決於一個人被治理的程度。德國哲學家約翰・奧古斯特‧埃伯哈德(Johann August Eberhard)是最早提出這種主張的人之一。他曾在一七八四年寫到,認為自治自由只存在於民主共和國裡,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偏見」。相較於自治國家的公民,開明君主的臣民享受許多──不,是更多──公民自治自由。正如埃伯哈德所指出的,在腓特烈大帝(King Frederick the Great)的治下,普魯士人比實施自治的瑞士人民享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卻繳更少的税。
是什麼引發了這種自由思想的轉變?為何限制政府權力的自由觀念取代了民主式的自由概念?當歷史學家思考這個問題時,他們傾向從歐洲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趨勢中尋找答案,因此人們常宣稱西方宗教寬容性的演變──宗教改革的意外結果──引發新的思考自由方式的出現,自由被等同於私人獨立性。另一種流行的說法則將這種關於自治自由的思想轉變,歸因於十七和十八世紀時市場經濟的出現,據說這導致人們形成一種更加開明的自由概念,此種自由概念以自然權利為觀念核心。但與人們普遍的假設相反,無論是宗教改革或是市場經濟的過渡,都不曾對關於自由的辯論產生太大影響。
正如本書所展示的,對於自治自由的新理解,是十八世紀末大西洋革命浪潮引發的長期政治鬥爭下的產物。這些革命在建立我們現代、民主的政治體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們也引發了反民主的可怕反應,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演變為政治暴力──恐怖統治(the Terror),更令大西洋兩岸的許多知識分子與公民行動者,群起反對推行自下而上的政治。由此而生的反革命運動開始傳播一種對自治自由的新理解,將享受私人獨立性置於優先地位,並透過這種理解直接挑戰了民主式的觀點。埃伯哈德對自由的評論就是個例子,他很直接反對那些「年輕的共和黨人」,因為他們希望推行仿效瑞士和美國的制度,藉此將普魯士民主化。
反革命運動對於自由的重新定義,回過頭來又影響了十九世紀初出現於歐洲的新政治運動,尤其是自由主義。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班傑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衷心同意保守主義者,如埃伯哈德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人的觀點,即認為民主不僅與自由截然不同,而且可能對自由有害。即使歐洲自由主義者最終接受了民主制度已是個既成事實,但他們仍持續堅持自由和民主是兩回事。他們主張,保護自由的最好方式不是擴大人民對政府的控制,而是設置障礙來阻止政府干預人民的生活,於是,在民主脈絡中,只有限制人民權力的制度與規範,才能最好地保護個人自治自由。我們可以肯定,這種觀點會令早期的自由鬥士們感到震驚。
當人們主張必須限制民主才能保衛自由時,如康斯坦這樣的思想家考量(在某程度上)的是弱勢少數族群,如宗教異議人士的立場。但以自由為名的反民主鬥爭背後的驅動力往往是恐懼,因為人們擔心新獲得選舉權的烏合之眾會運用國家權力來進行經濟的重新分配。在歐洲,這些憂慮在整個十九世紀不斷加劇,並於一八八○年代及一八九○年代達到頂峰。法國經濟學者保羅・勒華-波留(Paul Leroy-Beaulieu)提供我們一個例子,他曾哀嘆「西方文明」將很快受到一種「新農奴制」奴役,並警告現代民主國家的統治必然是基於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集體主義」的降臨及其對所有自治自由的破壞,則是不可避免的下場。
在美國,反革命的自治自由概念花了較長的時間才流行起來。儘管一些心懷不滿的聯邦黨人和保守主義的輝格黨人附和了這些關於自治自由的反革命觀念,但是大部分的美國人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仍擁抱作為革命核心的民主式自由概念。然而,這種情況在美國內戰後隨即發生了變化。由於選舉權擴大到自由民,以及大批移民來到北方,菁英對於民主制度的不滿增加了,因為突然間,大批的黑人及新移民開始要求享有那些菁英極不情願承認的政治權利。鍍金時代(Gilded Age)時,只有透過最大限度節制大眾權力,才能最好地維護自由──這樣的觀念在美國廣泛流傳開來。此一時期的領袖人物,如頗具影響力的耶魯大學教授孫末楠(William Graham Sumner)即強烈反對將自由等同於民主自治的觀點。孫末楠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或者是英語直白的說法「管好你家的事」,才是「自治自由的信條」。
詆毀民主的人所闡述的新自由願景並不是從來沒有遭遇反駁。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的長蕭條(Long Depression)後,大西洋兩岸有愈來愈多的激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及進步主義者,拒絕了將自由等同於最小政府的想法。他們認為那種自由是虛假的自由,只是捍衛階級利益的單薄無力說詞而已,要讓人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必須終結政治與經濟的支配。尚・喬黑斯(Jean Jaurès)及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等思想家和政治人物於是重振了民主式自由的革命呼聲,並將之擴展至經濟領域。然而,一九四五年後,冷戰壓倒了這些聲音,「自由等同於最小政府」的看法甚至得到許多左傾知識分子、政治人物及選民的接納,直到今天亦然。
正如這個簡略的概述所暗示的,理解自由的悠久歷史首先令我們注意到,自由這個概念被等同於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是多麼晚近的事,但這段歷史也揭示出關於我們如今思考自由的方式,其系譜學的一個關鍵。今天常見的自由觀念,例如:縮小政府的範圍才能最好地保護自由等觀念,其發明者並不是十八、十九世紀的革命者,而是他們的批評者。今天最熱情的自由鬥士,樂於將自己描繪成締造我們現代民主的革命者的繼承人。但從他們對最小政府的呼籲來看,當代的自由愛好者其實更像是民主的敵人,而不是它的締造者。他們是埃伯哈德、孫末楠的繼承者,而不是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和弗里德的傳人。
一些基本卻重要的細節
自由是種崇高的理想,向來為詩人、藝術家及哲學家這類人所歌頌。但自由也是種可怕的意識形態武器,凡是過去幾十年來一直關注美國及其他國家公共辯論的人,都可以毫不費力地舉出無數自治自由被用來達到各種政治目的的例子。權威人士將他們不同意的制度和政策,等同於對自治自由的威脅。政治人物控訴自己的對手愛自由愛得不夠深,海外國家和行動者被貼上危害國家自治自由的標籤,如此他們才能爭取到更多對其採取軍事行動的支持。
本書要講述的,就是這種意識形態武器是如何在古代就被鍛造出來,於文藝復興時期重新出土,並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得到改造的故事。人們將清楚看見自由的歷史,不是一群白髮蒼蒼的哲學家擠在象牙塔裡,進行不痛不癢的辯論。相反地,自由的故事是激烈政治鬥爭的故事,在這些鬥爭中,有些人失去了他們的頭顱──這種說法毫不誇張。舉個例子,羅馬政治人物、自詡為自由鬥士的西塞羅,他的頭就被砍了下來,釘在古羅馬廣場(the Forum)的帝國講壇上。在這些鬥爭中,人們發明了各種不同的自由概念,彼此誓不兩立。
簡言之,本書主要著重於自由作為一政治概念的發展過程。我追溯了針對以下這些基本問題不斷在變化的答案:何種政治制度能讓我們過自由的生活?一個自由的國家是什麼樣的?這意味著自由歷史的其他許多面向,得到的關注較少,尤其是關於何謂法律自由的那些辯論(法學家如何區分自由人與奴隸,以及哲學家如何去正當化或批評這些差異),多半都超出了本書的討論範圍。關於道德自由的辯論也是如此,其思考的是在何種程度上,個人才是真正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
這並不是說這些問題不重要。首先,歷史學家都同意自由觀念的誕生,一開始就是為了要指出奴役與法律束縛之間的對立。語源學上的證據也可以說明這點,Eleutheros是希臘語的「自由」,源於印歐語中的†leudh-,意為「屬於人民」。拉丁語的liber可能也來自同樣的字根。這表明古代的自由概念是作為奴役的反義字出現的,因為人們對自由的理解,在於大多數的奴隸是外國人或外鄉人,因此不屬於人民。文字紀錄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觀點。在現存最古老的希臘文獻、荷馬(Homer)的史詩《伊里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yssey)中,名詞與動詞的「自由」這類的字,一直被定義為「奴隸」與「奴役」的相反面。
因此,自由概念乃是作為一個法律分類而誕生:自由就是成為奴隸的相反。在自由的歷史中,為了定義和正當化這些不同分類的嘗試,顯得極為突出。法律束縛的存在,產生出許多引發激烈辯論的倫理與實踐難題。法律學者及哲學家就誰才能被視為自由、誰不能,以及成為奴隸意味著什麼的問題,屢屢發生爭執。也許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正當化自由與奴隸之間的區別──如果這種區別存在的話。例如:早在西元前四世紀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就已經在思考奴隸制是否具有倫理正當性的問題了。他認為在特定情況下答案是肯定的,但這一問題仍持續在不同年代引發人們的激辯。
道德自由的課題也是類似的情形,它曾是倫理學中最熱門的討論話題之一(至今仍如此),吸引了來自各種知識傳統及歷史背景的哲學家和神學家的參與。他們的探究圍繞著一個永恆的提問:人類有自由意志嗎?或者,我們是否一直受到我們無法掌控的力量所統治,比如我們的激情、生物反應,或是天意?這是季蒂昂的芝諾(Zeno of Citium)哲學的中心問題,季蒂昂的芝諾是斯多噶學派的奠基者,於西元前三世紀書寫了他的主要著作。將近兩千年後,英國思想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仍在和同樣的課題進行搏鬥。
這些辯論及其歷史雖然本身十分引人入勝,但已經得到了其他歷史學家的廣泛探討,他們的成果不須在此重述。例如:本書將不會企圖去解釋,為何大多數西方人不再認為將人視為動產的奴隸制,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也不會去仔細考察自由意志這一觀念的起源。取而代之,我將追溯多個世紀以來關於「在一個社會中,或者是作為一個社會,人如何獲得自由?」的漫長辯論。比起在國際領域,我主要關注的是政治思想家如何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在一個城邦國家或主權國家裡,將自由制度化。正如我們會看到的,在這個故事的後半段,這些問題也激發了關於如何將自由延伸到經濟秩序的反思。
這就引出了我要說的第二點。正如前面提到的,本書聚焦於傳統上認為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歷史,這並非是因為只有西方哲學家才思考,在一個社會中或者作為一個社會,自由意味著什麼,無分古今中外,人們都曾思考過這一課題。例如:印尼的航海民族瓦久人(Wajo’)就極為珍視政治自治自由,在他們的十八世紀編年史中,有好幾處提到了自由或merdeka的重要性。merdeka這個字源自梵語,在馬來語及相似的語言,如布吉語(Buginese)中,被用於表達與「奴隸」相反的「自由」的意思。根據這些編年史,瓦久的一位奠基元勳曾宣布:「瓦久人民是自由的;生而自由。」瓦久人也很清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們的編年史指出,為了確保自由,有三件事至關重要:「首先是不要干涉人民的意願;其次是不要禁止意見的表達;第三是不要阻止(人們去,譯按:括號內容為作者所加)南方、北方、西方、東方、上游或下游。」
然而,這本書專注於西方的思想家與辯論的原因,更多是與我自己的專業侷限有關,除此之外,也有更實質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當涉及世界各地的人民思考或談論自由的方式時,相較於其他可比較的傳統,西方政治傳統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例如:在阿拉伯語世界中,自由(hurriyya)的概念在整個十九世紀,就隨著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增加,尤其是法國,而變得愈來愈政治化。同樣地,在日本,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等歐洲思想家作品的譯介(彌爾的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日語版於一八七一年出版),也激起了關於自治自由之本質與意義的新辯論。對於西方自由傳統發展的歷史性理解,也因此與更廣泛的當代自由辯論產生了直接的關聯。
就這點而言,也許說清楚當我談到「西方」或「西方傳統」時想表達的意思,是有用的。近年來,柯斯塔斯・馮拉索普洛斯(Kostas Vlassopoulos)等學者已經注意到一種西方主義(Occidentalist)意識形態的存在,這種意識形態錯誤地假定「世界歷史上存在著邊界清楚的實體」,如西方和東方,自古以來就在那裡,就像大陸和其他自然現象一樣。我努力在本書中避免西方主義的陷阱,強調思考自由這個西方傳統的出現,絕不是一個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的現象。取而代之,我會展示這個傳統是如何通過絕大多數歷史能動者隨機制宜(contingent)的行動而形成,同時強調這一傳統的地理與時間界線,是如何歷經各年代仍持續受到爭議。
舉例來說,近代早期歐洲人是否自認傳承了某種由古希臘和羅馬人所構想、以自由為中心的願景,這一點就絕對沒有明顯的答案。羅馬帝國滅亡後,頌讚自由為最重要政治價值的希臘和羅馬文獻,數世紀以來無人閱讀。許多開始閱讀這些文獻的近代早期歐洲人所居住的地區,從未屬於羅馬共和國的一部分,更別說希臘世界了。此外,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也和古代人有顯著不同。這些古人的文字似乎又開始與後來的歐洲人產生關聯,但這並不是因為某種西方傳統中牢不可破、與生俱來的一體感發揮了什麼作用。近代早期的人們對古代自由概念會重新燃起興趣,其實是一連串隨機制宜的事件所導致。
首先,如果沒有考慮到一個由學識豐富的男女組成的小團體──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人們就無法理解古代自治自由的復興。跟隨著十四世紀義大利詩人佩脫拉克(Petrarch)的足跡,人文主義者出於自身的原因,開始相信古代希臘與羅馬文本代表了人類文明的頂峰。人文主義者因此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來傳播這些文本,並在這過程中建立了一個以研究西塞羅、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Livy)等古代作家為基礎的教育體系。這些雖然是深思熟慮的選擇,但絕不代表是預先決定好的。同樣重要的是,人文主義思想傳播的時間,正好疊合了十六、十七世紀發生的大規模政治動盪,這些動盪令人們覺得有需要以新的方式來思考政治。沒有這個巧合,古代思考自治自由方式的復興,可能不會在歐洲政治思想上留下深刻痕跡。
西方傳統這個概念,也不是源自對希臘羅馬理想的忠貞不二。在法國大革命的餘波下,許多人開始認為企圖貫徹如何過上一種自由生活的古代觀念是種誤導,甚至具有危險性。作為對此種思考的回應,康斯坦等人提出了一種新的自由系譜學。在他們看來,人們不應將現代、西方的自由概念,理解為希臘羅馬文明的遺產,因為關於自治自由的「現代」思考方式與古代的自由概念截然不同──實際上,是根本相反。於是康斯通重新概念化了自由的西方傳統,在他的描述中,自由是為了反對那個古代傳統而誕生,而不是根植於那個傳統。
同樣地,西方的地理輪廓也成為爭辯的話題。儘管當前大多數人在談到西方時都將法國包括進來,但是在美國德裔思想家法蘭西斯・李伯(Francis Lieber)的暢銷著作《論公民自治自由與自治》(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中卻不是這樣看的。他主張康斯坦對古代與現代自治自由的區分,跟另一種二元思維重疊,即英國國教派(Anglican,譯按:主張從天主教獨立出來)與高盧天主教派(Gallican,譯按:主張限制教皇權力)之間對自由的觀念差異。儘管高盧天主教人士執著於古代的思考方式(主要是受到盧梭的有害影響),但英國國教派(英國人和他們的美國後裔)卻發展出一種真正對自治自由的現代理解,這要歸功於他們的新教和條頓人(Teutonic)的傳承。換句話說,李伯深思熟慮地將現代西方的範圍限制在英語世界中
長話短說,就我們可以談論政治思想史中的西方傳統而言,我們需銘記在心的是:這個傳統是被建構出來的,也是受到爭議的。然而這並不會讓這個傳統變得不「真實」,也不會令西方這個概念變得不再有用。今天,許多人都明白他們對自治自由的觀念,本質上是西方的──是從希臘和羅馬人、十八世紀的那些革命,直到現在一脈相承的產物。一部關於自由的思想史,必須說明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同時也要揭露這個傳統隨機制宜的本質,以及支撐著這個傳統、那些挑起爭論的主張。
最後一條編輯台講述:一些讀者可能認為這本書的目標(概述從古至今的自由歷史)太過雄心勃勃,也許甚至不可能實現。人們可能會說,透過追溯一個概念在這麼長一段時期的歷史,一個人可能會創作出一部脫離現實血肉的歷史,其中的概念和思想成了自己歷史的演員,創造出它們的男男女女反而不是重點。除非人們願意接受黑格爾(Hegel)的觀點,認為觀念是世界歷史的推動者,否則這必定會產生出糟糕的歷史;或者如英國思想史學者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說法,這種方法產生出的故事更容易被歸類為神話,而不是歷史。在觀念史裡的這類神話故事中,歷史行動者被迫為他們不可能有的動機和意圖負責──例如:他們會被迫參與特定觀念的「闡述」或「推導」過程,但他們根本不曾了解過這些觀念。
但正如歷史學家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彼得・高登(Peter Gordon)以及達林・麥克馬洪(Darrin McMahon)近來主張的,這些危險雖然真實,卻不是無法克服。「大」思想史的復興從實踐上說明了這點。只要觀念史學者牢記她所重述的這段歷史是由一群人創造出來的,這些男男女女各自有其特殊、受到脈絡限制的原因而這樣做,就應該可能避開將歷史變成神話的陷阱。具體說來,我認為我們可以透過密切關注觀念的傳播與接受,透過用證明的方式,而不是將意圖強加給歷史能動者;以及最後,透過將意義的變化歸因於有紀錄可循的歷史行動者的意圖,而不是相關觀念的某種內在邏輯,來避免將歷史變成神話的危險。例如:當我宣稱十八世紀革命者援引了古代的自由概念時,我能證明他們可以接觸到那些古代文本,而自由概念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我也可以證明他們認為自己正在參與一場實踐工作,目標是復興與古代相關的自由概念。
除了這些方法論上的考量之外,這個研究範圍的計畫還會涉及其他風險。當然,在寫作這本書時,我不得不接觸遠超出我原本專業領域的知識,即十八、十九世紀的法國政治思想。這樣的努力的確有其風險,但我也相信承擔這些風險是值得的。因為只有當我們能從「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角度來看待自由的歷史,也就是將其視為從古希臘開始、持續至今的一場辯論時,我們才能真正掌握將自由概念化為「有限政府」這一思想的新穎性──同時我們也才能認識到這個概念的創新,其背後的反民主動力。
NT$545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