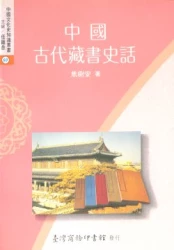自己的歷史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
商品編號:07000012
定價: 430 元
優惠價: 79折 339 元
優惠活動
購買提醒
本商品為出版已久的書,出版已久的書容易產生些許的黃斑、或有些許瑕疵(例如:壓痕、褪色等),不影響內文閱讀。每本書況不盡相同,請考慮評估後再購買結帳,採取隨機出貨。
如想進一步了解書況詳情,可以來信 cptw1897@gmail.com ,或點擊右上角「 客服 」留言詢問,感謝您支持臺灣商務印書館。
內容簡介
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
余撰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
—嚴耕望
嚴耕望(1916~1996),歷史學家,專治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在二十世紀中國中古史領域中,繼呂思勉、陳垣和陳寅恪等大師之後,臺灣無疑是由嚴耕望領軍,接續前人之大業。余英時稱其集錢穆、陳寅恪、陳垣、呂思勉四大家之長於一身,並讚譽嚴耕望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最佳史學入門書
《治史三書》含括先生所作之《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及《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這三本書總結了嚴耕望一生從師問學的歷程與研治史學的方法,是治史者重要的入門書。本書內容涉及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論文體式、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論文撰寫與改訂,以及努力途徑與生活修養等諸多問題,語言質樸流暢,淺顯易懂,力求實用。
★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書中更可見其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傳統學人風範,在物慾橫流的時代,自甘邊緣,安貧樂道,從學術中尋求自足,非內心極度強大者絕難做到。
★歷久彌新的史學價值
嚴耕望先生未留下自傳,但本書談及作者求學治史之歷程,可謂先生之學術自傳。在《治史三書》中,記述先生長達六十年的治史過程,史界的變遷以及與當代史家的互動紀錄,亦為重要的現代史料。還有先生對百餘部史料的點評更是後人重要的珍寶。凡此種種都讓《治史三書》不但未隨潮流隱沒,更添歷久彌新的史學價值。
★嚴耕望先生治史格言
● 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
● 盡量少說否定話。
● 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 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
● 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
● 引用史料要將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斷章取義。
● 儘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後期改編過的史料。
● 「無孔不入」、「有縫必彌」。
作者介紹
嚴耕望
嚴耕望(1916~1996)
安徽省桐城縣人。
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歷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助理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史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耶魯大學訪問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講座,東吳大學特約講座,新亞研究所教授等職。197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96年於台北忠孝醫院逝世,享年八十歲。余英時先生在悼念文章中稱他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著有:《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兩漢太守刺史表》、《唐僕尚丞郎表》、《唐史研究叢稿》、《唐代交通圖考》、《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等書及學術論文百餘篇。
目錄
卷一 治史經驗談
序 言
壹 原則性的基本方法
貳 幾條具體規律
參 論題選擇
肆 論著標準
伍 論文體式
陸 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
柒 論文撰寫與改訂
捌 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
玖 生活、修養與治學之關係
校後記
卷二 治史答問
序言一
序言二
我研究歷史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
我在中學大學讀書時代的課外閱讀
我對於政治制度史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
我對於歷史地理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我對於上古史與考古學的興趣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
我對於唐詩史料的利用
我今後的撰述計畫
研究歷史不要從哲學入手
研究中國史不必要從中文入手
社會科學理論只是歷史研究的輔助工具,不能以運用理論為主導方法
「無孔不入」、「有縫必彌」
目錄學與校勘學
年齡與撰述
前進與落伍
史學二陳
通貫的斷代史學——呂思勉
翻譯工作的重要性
我購藏書刊的原則
我對中國通史講授的幾點意見
附錄一 嚴耕望先生訪問記 黃寬重
附錄二 唐代交通圖考序言
附錄三 著者其他論著目錄
卷三 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序言
上篇 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
下篇 從師問學六十年
附錄一 我與兩位王校長
附錄二 我對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試閱
壹
原則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說過,治史不能機械的拘守某一類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則大方向。我覺得治史學有幾條應注意的原則性的基本方法問題,也有一些應注意的較具體的規律。茲先就原則性的基本方法問題提供一點意見。
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
專精與博通兩個概念當為一般人所知,不必說;但尤著重「精」與「通」兩字。專不一定能精,能精則一定有相當的專;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當的博。治學要能專精,纔能有成績表現,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學愈來愈走上專精之路,要成為一個專家;雖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際的研究,但過分重視專精的觀念仍然未改。其實,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各種學問都當如此,尤其治史;因為歷史牽涉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當博通,就不可能專而能精,甚至於出笑話。所以治史最為吃力,很難有一個真正的青年史學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從兩方面談。第一、史學本身的博通。即對於上下古今都要有相當的瞭解,尤其對於自己研究的時代的前後時代,要有很深入的認識,而前一個時代更為重要。若治專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經濟史、社會史、學術史等等,治某一種專史,同時對於其他的專史也要有很好的瞭解,至少要有相當的瞭解。第二、史學以外的博通,也可說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種社會科學。
先講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種社會科學,雖然斷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對各方面有一點皮毛知識,有一點總比毫無所知的好。現在時髦的看法,要以社會科學的觀點研究歷史,於是各種社會科學家都強調自己的立場,以為研究歷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論不可。記得前年台灣有些史學家與一些社會科學家開過一次聯席會議,社會學者、人類學者、經濟學者、統計學者、心理學者等等,就各人強調自己的方法理論,作為研究歷史的法寶。當時有一位歷史學者說,這樣講來,我們歷史學者就無用武之餘地了!其實各方面的意見都有問題。治史有考史、論史與撰史的不同,而相輔為用。考史要把歷史事實的現象找出來,論史要把事實現象加以評論解釋,然後纔能作綜合的撰述工作。社會科學的方法對於論史最有用,對於考史撰史的用處比較少,社會科學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論史工作,考史撰史還是非全部由史學家做不可!至於各種社會科學對研究歷史都有幫助,那是絕對正確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隨時都可用得上。幾年前有一位頗有名的史學界朋友,告訴我:「要用統計法治史」。這話本不錯,但史學問題那都是統計法所能解決的!其實我最喜歡用統計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漢代地方官吏的陞遷,就是用的統計法,根據統計數字,作成陞遷圖 ,在那時可謂是極新的方法了。但歷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難道不能量化,我們就不做?現在我寫「國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歡用統計法,還特別搜購了一部《地理統計學》來看。那裏面所講的方法非常好,但歷史已過去了,很少如意的資料讓我統計!所以方法雖好,但材料不允許,用不上,奈何!用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的方法理論治史學,也同樣都有局限性。有些人從政治學的觀點批評政治史學家的成績,從經濟學的觀點批評經濟史學家的成績,從社會學的觀點批評社會史學家的成績,總覺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實際的苛責。他們忽略了歷史已成過去,人家那種成就也許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那有社會科學家研究目前的人類社會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與方法去作調查,材料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那樣方便!然而我們不能否認有些社會科學的知識對於研究歷史實有極大用處。就以我的經驗言:我在高中讀書時代寫了一篇〈堯舜禪讓問題研究〉,我認為堯舜禪讓只是部落酋長的選舉制,這就是從人類學家莫爾甘(L. H. Morgan 1818-1881)所寫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悟出來的。儒家不瞭解當時實情,比照後代傳子制看來,堯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禪讓,這是美化了堯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奪漢獻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漢獻帝寫一張最後詔書,說是把天下讓給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說舜之代堯,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樣的篡位而已;這又把堯舜故事醜化了。但我若沒有一點人類學知識,就極可能不能悟到這一點。又例如我撰〈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 ,說明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職權地位之不同,以及兩類機關的關係。按唐代六部與九寺諸監的職權似乎很混亂,一千多年來都搞不清楚而有誤解。我詳徵史料作一番新解釋,說六部是政務機關,六部尚書是政務官,九寺諸監是事務機關,他的長官是事務官,這兩類機關有下行上承的關係。如此一來,各方面看來很不合理的現象都變成合理了,這也是從近代行政學的觀念入手的。舉此兩例,可見社會科學對於歷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會科學的科別也極多,每一種學科都日新月異,一個歷史學者要想精通各種社會科學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過我們總要打開大門,儘可能的吸收一點!儘可能予以運用!縱不能運用,也有利於自己態度的趨向開明!
至於歷史本身的博通,更為重要。但這是本身問題,要博通比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從兩方面講。第一是消極的,可使你做專精工作時不出大錯、不鬧笑話。我舉兩個例如下:
其一,法國藏敦煌文書第3016號紙背云:
「天興(?)七年拾壹月,于闐迴禮使、內親從都頭、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檢校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索全狀文。」
日本有一位敦煌學專家屢次提到此條,以為北魏道武帝天興(他釋為天興)七年(西元404),當為敦煌文書之最古者。其實大誤。我們只看索全的官銜,馬上就可知道這一文件不可能早過晚唐,可能是五代時期的。何以見得?上柱國的勳名創自北周,朝廷中幾個功勳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賜,知此文件絕不能早在北周之前。以一個縣令擁有「御史大夫、校檢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的頭銜,那就不會早過安史之亂;又有「迴禮使,內親從都頭」的銜名,那就不會早過晚唐,所以至少「天興」二字當有一個模糊不清,他誤釋為「天興」了。其實這些官銜,在兩《唐書》、《五代史》中常常見到,都在安史亂後,尤其晚唐以後,安史亂前是絕不一見的,所以不必是講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書,就該對於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歷史各方面都有相當瞭解,然而他事實上只在敦煌文書那一小點上去鑽,所以出此大錯!
推薦序文
我對於歷史發生興趣,當追溯到高中讀書時代聽李師則綱的一次講演,題目大意是「歷史演進的因素」,同時又讀到梁任公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後來也讀了些西方學者史學方法論之類的編譯本,所以方法論對於我的治史不無相當影響。不過當我在中國歷史方面工作了幾十年之後,總覺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講方法,但絕不應遵循一項固定的方法與技術。只要對於邏輯學有一些基本觀念,如能對於數學有較好的訓練尤佳,因為數學是訓練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學問總不外是個「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地仔細閱讀有高度成就的學者的好著作,體會作者探討問題的線索,然後運用自己的心靈智慧,各出心裁,推陳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至於方法理論,不妨讓一些專家去講,成為一項專門之學,但實際從事歷史事實探討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過拘守。太過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紙上談兵,並無多大用處。
大約是一九七四年冬,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邀我作一次講演,內容希能與史學方法有關。我既不太講究方法論,對於此項邀約自然不很感興趣;但辭不獲已,只得就自己治史經驗作簡略報告。為欲使諸生能實有受益,所以先寫綱要,油印為講義。綱要分上下兩節,上節談幾條原則性的基本方法,下節談幾條具體規律。後來又就此類問題在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班上談過一兩次。一九七六年七月應《中國學人》編者之約,就講義上節,草成《治史經驗談》上篇,在該刊第六期發表。明年續成下篇,以該刊久未出版,而半篇論文未便改投他處,所以迄未刊行。
自上篇發表以來,頗受一些青年讀者的重視,促能多寫一些此類文字;乃想就平日與諸生閒談中涉及有關治史經驗諸問題而為前兩篇所未論及者,續為寫出,對於青年史學工作者或有一點用處。今年七月初,自美國遊罷歸來,趁未開始研究工作之前,一口氣寫成〈論題選擇〉以下七篇,並就舊稿續作改訂,分別為篇,與新作合編為一小冊,仍題曰《治史經驗談》。回憶楊聯陞兄一次來港,閒談中謂我對於後輩青年當有較大責任。此語對於這本小冊的寫作,可能也有催生作用。朋友相勉,特以識之。
這本小冊,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問題,隨意漫談,說不上史學方法論,充其量只能說是我個人的體驗、個人方法而已。綜合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幾點。原則上: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以具體問題為先著,從基本處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則,不依傍,不斥拒,能容眾說(包括各種理論與個別意見),隨宜適應,只求實際合理,不拘成規。方法是:堅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為巧,以慢為快,聚小為大,以深鍥精細為基礎,而致意於組織系統化。目標在:真實、充實、平實、密實、無空言、少皇論,但期人人可以信賴,有一磚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輝光則心嚮往之而已。最後一篇特措意於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要鍛鍊自己成為一個健康純淨的「學術人」,此實為學術成就的最基本條件。至於探索問題的技術,則本編甚少涉及。因為技術細節,很難具體言之。大約論題若能以述證方式,排比材料,即可達成結論者,較易為功;若是無直接有力證據,必須深一層辯論證實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無孔不入(此謂攻,謂建立一項論點,非必攻擊別人論點),有縫必彌(此謂守),務期自己論點能站得穩,無懈可擊。這就要隨宜運用匠心,解決問題;但很難歸納出幾條方式,具體扼要言之,所以也很難以筆墨相傳授;目今講壇一般教學方式也很難傳授。只有古人學徒方式,學生即在身邊,遇有使用細緻技巧處,隨時指授,較易見功。但此種學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過去,今日青年好學者若想學習前人研究技術之精微處,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細閱讀,用心揣摩,庶能體會;若都只匆匆翻閱,一目十行,只能認識作者論點,至於研究技巧,曲折入微處,恐將毫無所獲!我在中文大學研究院「中古史研究」課堂上常提出研作較精之論者,就其探討入微處,為諸生講解,立意即在幫助青年揣摩他人精品的研作技巧,以為他們工作之一助;但亦惟程度較高,好學深思者,能欣賞,有受益;一般青年似仍少領會!好在一般論題只用述證方式已可解決,必須深入曲折辯論者究占少數;而且現今寫論文,能深入曲折辯論者已較少,能欣賞的人也不多,蓋學風日下,率就淺易,此如歌唱,時代曲流行,京劇演員吃力不討好,因此我也不想花太多功夫在此等處多費筆墨!
近五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界,人才輩出,朗若月星;爝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學鉅子多半天分極高,或且家學淵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後來學子可能自嘆不如,不免自棄。我的成就雖極有限,但天賦亦極微薄,一切遲鈍不敏,記憶力尤壞,幼年讀書,三兩百字短文亦難熟誦。老妻曰,無聰明,有智慧;這話適可解嘲!相信當今能入大學受教育的青年,論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舉我小成之經驗與生活修養之蘄向以相告,或能有一點鼓勵作用!所以毅然違背我一向做人原則,不揣淺陋,不避自伐之嫌,將自己的工作經驗獻給青年史學工作者;是否有當,實際有用,在所不計!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序於香港沙田吐露港西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十月二十日增訂再稿於九龍塘獅子山下霞明閣寓所;八○年四月十五日三稿畢功。
NT$339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