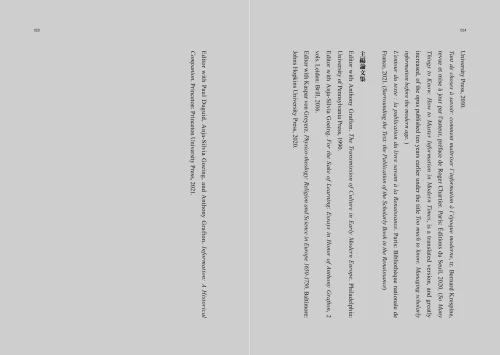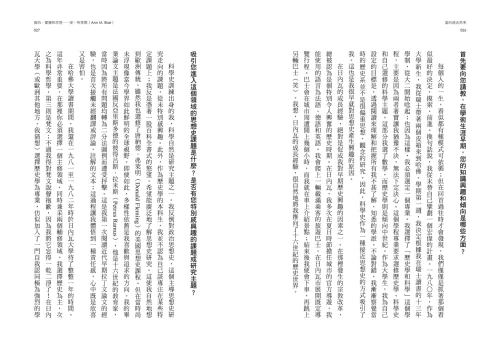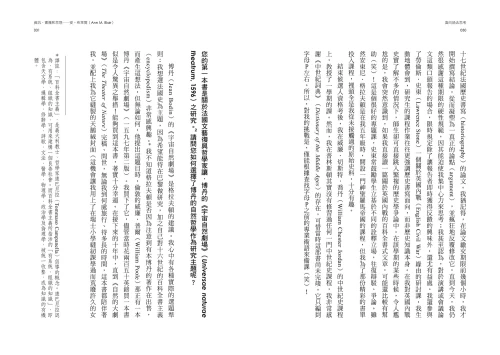面向過去思考:與史學大師的爐邊閒談,打造歷史思惟的八場對話
商品編號:06030153
定價: 450 元
優惠價: 66折 297 元
優惠活動
內容簡介
波薩獎得主安東尼.格拉夫頓、昆丁.史金納、塞雷納獎章得主吉爾.克雷耶、安.布萊爾、洛林.達斯頓、班傑明.艾爾曼、彼得.米勒、讓-路易.貢當
八位重量級學者親自分享,踏入歷史學這門領域的學思歷程!如何汲取前人智慧,解決眼前難題?如何拋開學科框架,拓展思考深度?如何因應時代演進,調整研究方法?
歷史學並非蓋棺論定的遊戲,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思惟方式。讓我們一起進入史學大師的思考領域,揭開歷史學技藝的神祕面紗。唯有立足現在,思索過往,才能邁向未來!
本書作者亞歷山大‧貝維拉夸和費德里克‧克拉克兩位年輕學者,訪問八位當代歷史學界的大師。他們彼此來自不同的史學領域,包含書籍史、科學史、非西方知識傳統的歷史、學術史、哲學史、古物學和物質文化的歷史、宗教史、以及政治思想史。透過問答訪談的形式,這些學者述說了他們投身歷史學的經驗,如何看待過去與現在的聯繫?如何突破既有的思惟,開創全新的視野?
例如:與談人之一的吉爾‧克雷耶教授,曾經在瓦堡研究所圖書館擔任十六年圖書館員。作為一位圖書館員,她必須掌握圖書館內所藏的書籍,讓她了解到學習歷史不能侷限在自己的舒適圈,要像一間圖書館一樣結合歷史、藝術、文學、哲學、科學等領域,才能臻於至善。
本書揭露歷史學家寫作背後的心路歷程,訴說他們的思想深度與廣度,不僅為以學術為志業的人們,提供一盞指引前路的燈火,更向大眾展現歷史學的本質,引領我們重新思考看待世界的方式!
作者介紹
亞歷山大.貝維拉夸(Alexander Bevilacqua)、費德里克.克拉克(Frederic Clark)
亞歷山大.貝維拉夸(Alexander Bevilacqua)
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歷史學助理教授。
費德里克.克拉克(Frederic Clark)
南加州大學古典學教授。
譯者簡介
徐兆安、陳建元、陳建守、韓承樺
徐兆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陳建元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譯有《羅馬的崛起》、《聖殿騎士團》、《想想歷史》、《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合譯)等書。
陳建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共同創辦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韓承樺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名人推薦
蔣竹山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涂豐恩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StoryStudio」創辦人
「在這個被金句和推特主導的時代,我們很難不得出一個令人憂鬱的結論:人文學科處於危機之中,而學術不再是一種精神志業。本書則給了我們堅持信念的理由。我們彷彿置身與畫像僅有咫尺之遙的肖像畫廊,與八位傑出的近代早期思想史家,親密地面對面交流。在這些談話中,我們再次被提醒了博學和語文學追求精確性的這些傳統美德,即使在歷史學思惟似乎受到圍攻的這個時代,這些美德仍舊支撐著這個領域。」
彼得‧戈登(Peter E. Gordon),哈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書針對當代好幾位近代早期思想史最優秀的學者,進行了深入訪談,本書對於研究各個時代與地區的學者而言,都會是有益且令人愉悅的。貝維拉夸和克拉克梳理了思想史學界研究的現狀,以及不同的思路和其他各種另類的實踐模式,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起源中是如何融合和衝突的。儘管針對近代早期歐洲的研究,一直以來是我們在討論該如何撰寫思想史時的爭辯核心,但一些學者預測,在未來,歐洲歷史的重要性將與日遽減。這是本引人入勝的書。」
山繆‧莫恩(Samuel Moyn),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這本書的核心是要將八個傑出思想史實踐者的經驗,轉化為能夠指導下一代思想史家的文本……這是本平易近人的書,相當適合被編入大學高年級的思想史或歷史方法的課程中,也可以作為研究生課程的補充教材,讓學生在閱讀作者專著時一併閱讀……這本書也捕捉住了一場傑出學術會議背後的精神。不鑽研這個領域的一般學者們,也將會發現這本書相當實用且饒富趣味。」
布萊恩‧班克斯(Bryan A. Banks),《法國歷史評論》(H-France Review)
目錄
目次
導言
資訊、書籍和思想──安‧布萊爾(Ann M. Blair)
拒絕不證自明──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
從「中國沒有什麼」,到「中國有什麼」──班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
總其技藝、方法為「學術」──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
哲學史作為一種研究的方式──吉爾‧克雷耶(Jill Kraye)
重新發現地中海世界──彼得‧米勒(Peter N. Miller)
教父學與古物學的交會──讓-路易‧貢當(Jean-Louis Quantin)
歷史與修辭──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
謝辭
試閱
歷史與修辭──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
昆丁‧史金納簡介
昆丁‧史金納,現任倫敦大學講座教授,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與皇家歷史學講座教授,曾獲波薩獎、沃夫森歷史獎(Wolfson History Prize)與俾勒非德科學獎(Bielefelder Wissenschaftspreis)等殊榮。史金納教授於一九四○年出生於曼徹斯特,他的父親是一位派駐於西非的殖民地行政官,母親則是一位學校教師。史金納教授以研究歐洲政治思想蜚聲於世,特別是關於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共和主義與馬基維利和霍布斯的政治理論等成果。史金納教授自謂其開展思想史研究之初,受到三位人物的影響:彼得‧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基斯‧湯馬斯(Keith Thomas)和約翰‧波考克(John Pocock)。史金納、波考克和約翰‧鄧恩(John Dunn)共同引領了被後人譽之為「劍橋學派」的學術運動。史金納的皇皇巨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I, the Renaissance, 1978),被認為是思想史上的經典之作,強調了將文本置於歷史脈絡中考察的重要性,並由此開展其「脈絡主義」的方法論。他借鑒英國哲學家奧斯汀(J. L. Austin)的「以言行事」(speech act)理論,認為歷史學家不僅必須分析政治文件的作者的意思(文件的行動意義),而且還必須分析作者在寫作中的「所作所為」(其言外之意)。
史金納教授的另一項研究主題是共和主義與自由,具體展現在《霍布斯與共和主義自由》(Hobbes and Republican Liberty, 2008)和《自由主義前之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1998)兩書。共和主義的歷史可以追溯至羅馬上古時代。史金納教授的分析重點主要擺放在歐洲歷史的近代早期,考察了馬基維利和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等人之思想中共和主義思想的重要性。他強調共和主義的重點實為個人行為不受他人干涉的消極自由,並且修正學界認為共和自由為積極自由的通說。不過,史金納教授指出,他的研究方案不是要用一種自由概念代替另一種自由概念,就好像它們超越了歷史一樣。相反地,史金納教授試圖挖掘共和主義的自由概念,藉以復原失落的政治可能性。除了學術研究的積累,史金納教授還負責兩套叢書的選編工作:「劍橋政治思想史文本系列」(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和「脈絡中的觀念」(Ideas in Context),皆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著作選編(專書、主編論文集)
專書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I,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譯本:奚瑞森、亞方譯,《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卷一):文藝復興》。新北:左岸文化,2004。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II, The Age of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譯本:奚瑞森、亞方譯,《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卷二):宗教改革》。新北:左岸文化,2004。
Machiavell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中譯本:蔡英文譯,《馬基維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by James Tull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中譯本:王加豐、鄭崧譯,《霍布斯哲學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譯本:李宏圖譯,《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譯本:李永毅譯,《馬基雅維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I, Renaissance Virtu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II, Hobbes and Civi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obbes and Republican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譯本:管可穠譯,《霍布斯與共和主義自由》。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Forensic Shakespe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inking about Liberty: An Historian’s Approach. Firenze: Leo S. Olschki, 2016.
Hobbes and the State. Assen: Koninklijke Van Gorcum, 2016.
From Humanism to Hobbes: Studies in Rhetoric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蕭高彥編,《政治價值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李強、張新剛主編,《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主編論文集
Editor with Peter Laslett and W. G. Runcima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2.
Editor with Richard Rorty and Jerome B. Schneewind. Philosophy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Editor.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中譯本:張小勇、李貫峰譯,《人文科學宏大理論的回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ditor with Charles B. Schmitt, Eckhard Kessler, and Jill Kra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譯本:徐衛翔譯,《劍橋文藝復興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Editor with Russell Price.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ditor with Gisela Bocks and Maurizio Viroli.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ditor with Nicholas Phillipso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譯本:潘興明、周保巍譯,《近代英國政治話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Editor with David Armitage and Armand Himy. Milton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Editor with Martin Van Gelderen. Republicanism: 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 Vol. I, Republican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ditor with Martin Van Gelderen. Republicanism: 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 Vol. II, The Values of Republican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ditor with Bo Stråth. States and Citizens: History, Theory, Prosp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譯本:彭利平譯,《國家與公民:歷史・理論・展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Editor with Alan Cromartie. Thomas Hobbes: Writings on Common Law and Hereditary Right (The Clarendon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Thomas Hobbes, Volume X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Editor with Hent Kalmo. Sovereignty in Fragment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Editor. Families and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Editor with Martin van Gelderen. Freedo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Volume I, Religious and Freedom and Civil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Editor with Martin van Gelderen. Freedo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Volume II, Free Persons and Free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Editor with Richard Bourke. Popular Sovereign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一開始是什麼吸引您研究思想史?而又是什麼特別吸引您研究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家?
在學校時,一位傑出導師約翰‧艾爾(John Eyre)的影響激發了我的興趣。他過世時《獨立報》(Independent)上刊登了全版悼文以茲紀念,標題為「改變人生的歷史老師」。總體上,我接受的是非常完善的中學教育。我進入了一所英國的公學,這個沿用至今的稱呼頗為別緻──因為它們當然是私立學校,我的父母付出了他們可能難以負擔的費用,給了我的兄弟和我如此優越的人生開端。我們學習了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中的各種學科,但在最後三年中,課程大綱變得高度專業化。在此階段,我完全專注於拉丁文、英國史及英國文學。
我們對英國史的學習相當深入,但有些重要的限制。其一是高階政治的敘事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另一則是我們僅僅專注於兩個形成時期:宗教改革和英國革命。我的學習因而僅限於一五○○年至一七○○年之間。這幾個世紀又被依次視為一個關於英國解放的輝格派故事,先是天主教教會,爾後又是斯圖亞特王朝的君主專制主義,這項敘事最終則以所謂的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作結。
不過,這些事件咸認具有某種「思想背景」。當我們學習到宗教改革時,我們會被要求閱讀一些在當時引起爭議的著作,包括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而當我們學習英國革命時,同樣要讀湯瑪斯‧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專制主義的主導辯解理由,並在約翰‧洛克的《政府論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見到一六八八年革命的正當理由。我當時買下了所有的文本,而我購買並寫著批註的書現在還留在某處。你問一開始是什麼吸引了我專門研究思想史,而我的回答是:我發現自己立即而無差別地迷上了這一切著作。從很久以前的那時起,我便發表了很多有關摩爾、霍布斯與洛克的文章。我有時認為我的學術生涯大部分,不過是在試圖解答我在青春期時最初思考的某些問題,提供更好的答案而已。
早年這些研究的結果是,當我在一九五九年到劍橋讀大學時,我已然是一位思想史的奉獻者。但如果你問的是什麼吸引我關注政治理論和近代早期的歷史,那麼答案恐怕不會很有思想興味。這僅僅是因為我最初投身的就是這些課題,它們從那時起便一直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什麼是您自早年以來,一直心心念念的問題?
我以前是個非常書呆子的男孩,或者可以說,我成為了這樣的男孩。我十一歲時罹患結核病,幾乎不治,讓我的早年教育中出現很長的空檔。我不得不躺在床上將近一年,我所能做的事就只有讀書和聽音樂。這項影響十分深遠,在我重返學校之際,我整個人蛻變了。在那之後,我非常想在學習上成功,最終我決定要當老師──我一直以來主要就是如此看待自己的。
不過,我必須承認,我一開始最著迷的學術問題,並非全部或甚至主要是政治或哲學性質的問題。我青少年時期對建築史充滿了濃厚的研究熱情,有個夏天,我甚至寫了本關於英格蘭新古典主義建築史的小書,並手繪了插圖。然而,我去劍橋大學時不可能成為一名建築史學家,當時劍橋大學幾乎不教這門課。但無論如何,我至少對自己研究的歷史時期相關的社會和政治理論,愈來愈感興趣,而我當時開始思考的問題從未停止困擾我:關於國家的概念、代議制的理念、政治義務的根基與限制,以及政治自由的性質與範圍。
您早年在劍橋大學的導師和老師有誰,而您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麼?
我的政治理論主要老師──在劍橋大學的說法中是「指導教授」,我每週必須向其繳交一份書面作業──是約翰‧布羅(John Burrow),他後來成為牛津大學的思想史教授。但是,我還修了彼得‧拉斯萊特的「霍布斯和洛克」、鄧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的「啟蒙運動和黑格爾」,以及最吸引人的沃爾特‧烏爾曼(Walter Ullmann)的「中世紀法律與政治思想」等講座課。然而,我最重要的導師有些並非我的老師,而是我的同代人。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約翰‧鄧恩,他後來成為劍橋大學的政治理論教授。鄧恩比我更快察覺到,我們大多數講師都強調少數經典著作,這表示我們學習這門課的方式可能並非最有啟發性。鄧恩早在一九六九年便寫出了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修正主義著作之一,他對洛克政治思想的研究現在仍是模範。
您如何看待廣博的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兩者之間的關係?
我認為思想史是人類心靈所有產物的歷史研究之名。因此,對我來說,思想史除了哲學史之外,還涵蓋藝術、建築、音樂與文學史,而政治哲學只是哲學史的一個分支。因此,我認為政治哲學史是分支的分支。
順帶一提,我喜歡「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這個詞,而非我青年時期最廣為使用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我剛開始發表時,大家談論的仍是觀念史,我自己在一九六○年代寫的一些文章中也用這個詞。然而,我是帶有諷刺意味去刻意為之,因為我想論證,嚴格來說,沒有觀念的歷史,而只有觀念以不同方式被運用的歷史。我認為強調許多思想史家不研究觀念也很重要。對我來說,繪畫史是思想史的一種形式,但是我不確定這是否屬於觀念史,因為許多繪畫與觀念無所關涉。我喜歡「思想史」的包容性,我現在總是用這些詞來形容自己,即便我知道這用法沾染上一種淡淡的、亦且可能自滿的歧義。
您早年學術生活中有哪些書籍和課程可謂是關鍵點?
我再次意識到,某些關鍵時刻是在中學而非大學時發生。在我去劍橋大學以前,已然有兩位對我影響深遠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就是其中一位。有段時間裡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尤其欽佩他的《西方哲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從方法論上講,我現在不得不承認,這本書有些「原始」:這只是一系列思想傳記的組成,他對哲學家的選擇也感覺有點隨意,除了這些哲學家是羅素最感興趣的人物之外。但對我來說,它第一次打開了整個令我入迷的學說世界。我記得我開始讀這本書後,想到應該做些筆記,最終發現我大概是抄寫了整部作品。
羅素吸引我的另一點是他的文采。羅素下筆可謂精彩透徹,筆鋒同時又帶有不斷的諷刺。我現在認為這是種傳統的英式風格,或許還是某種精英主義的寫作方式,但我必須承認,它在某種程度上仍是我的榜樣。當然,我無法模仿風格,但我肯定還是希望能盡量寫得清楚明白。我喜歡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說明文字應當如同一面玻璃。
柯靈烏是另一位我在中學時接觸其作品,且對我仍然十分重要的哲學家。我被要求閱讀他的《歷史的理念》(Idea of History),一部關於歷史哲學的遺作論文集。這又引領我閱讀他的《自傳》(Autobiography),這是部殘酷的辯論作品,我在其中見到了他關於「問與答的邏輯」的著名討論。[6]我從柯靈烏身上獲得了一個觀念,即不應將文本僅視為主張的主體;應當將其視為特定問題的答案。以這種方式來看,在哲學這門學科中我們不再見到一系列經典問題的不同答案。問題與答案反而都開始看來像在不斷變化。對哲學的研究似乎也不再像是研究經典文本之事。假如有部分的目的,是要復原任何特定哲學著作可以視為答案的問題,這便要求我們超越文本,將目光投向其形成之情境。與初讀柯靈烏時相比,我現在更加直接地提出這些想法,但它們早在略具雛形之際,早已在我身邊如影隨形。
在大學裡,有兩位專家的著作使我特別興奮。其一是拉斯萊特所編之洛克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於一九六○年首次出版。我在一九五九年開始大學課程,因此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讀到拉斯萊特的作品,開始研究洛克。檢視洛克寫作的情境後,拉斯萊特得以證明,儘管洛克的《政府論》首次出版是在一六八九年,但洛克早在接近十年以前開始起草《政府論》。因此,對該作是為慶祝一六八八年革命而寫的一般認知基本於斯瓦解,而又有必要再次問洛克為何創作了這部作品。拉斯萊特的答案是,在查理二世(Charles II)統治末期,獨裁的氛圍日益高漲,洛克試圖證明自己有權利抵抗獨裁專制統治。我之所以認為此分析引人注目,是因其驗證了洛克的《政府論》所計畫回答的具體問題。簡而言之,拉斯萊特的學術研究完全是柯靈烏的風格。
約翰‧波考克的《古代憲法與封建法》是另一部令大學時代的我感到興奮的學術著作。波考克展示了一種特別的英國史解讀方式──在其中將議會視為憲法自古以來的特徵──是如何被用來挑戰英國革命前數十年中,走向專制主義的潮流。正如波考克明確指出的,有關議會的此一主張在證據上值得懷疑,但這對議會起因的意識形態價值,最終助其獲得接納。我認為或許就是這點,讓我開始思考與政治理論相關之意識形態,以及兩者之間是否有明顯區別。這成為了我一篇早期文章的課題,從那時開始,我發展出了這樣的意見:即使是最抽象的政治哲學作品,通常也能展示出其中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成分。我們可以放心假設,其目的在於讓某些既有的政治安排或承諾,獲得或失去合法地位。為了說明此一意見,我轉向霍布斯的哲學,一般會認為霍布斯超越於論戰之上。我試圖證明霍布斯深陷於他那個時代的政治辯論,以及政治理論史或許基本上就是這種論戰的歷史。
而就我大學時期的同儕團體而言,我們都在讀維根斯坦。維根斯坦於一九三九至四六年期間任劍橋大學的哲學教授,並於一九五一年逝世。他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於其過世後出版,被譽為本世紀最偉大的哲學著作,我現在仍然覺得沒錯。在我讀大學時,劍橋裡任何對哲學感興趣的人都在讀這本書。我認為我們主要將其視為關於意義理論的作品,儘管其中涵蓋的主題顯然很廣泛。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部分肯定是,維根斯坦勸告我們不要談論意義,而要追索字詞在語言遊戲中,以及構成生活形式時的運用。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一九六二年我剛開始研究時,奧斯汀(J. L. Austin)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出版。維根斯坦曾說過:不要問意義,要問可以運用什麼字詞和概念來行動。奧斯汀接著問:我們可以運用字詞進行的事情到底有多少?我發現奧斯汀得出的類型學正好若合符節我的目的。我認為他要告訴我們,語言有兩個不同的面向,因而有兩個不同的詮釋任務。一方面是字詞及其意義,而另一方面奧斯汀則稱之為話語之力。因此,無論話語為何,對說話者發言時可能在做的事進行解碼,就成了一項重要的解釋任務。奧斯汀在此處潛在的假設──需要將寫作和言語視為社會行為的形式來評判──提供了我從那時起一直努力遵循的基本詮釋學原則。
您投入研究的兩位關鍵人物是馬基維利和霍布斯,這很令人印象深刻,因為他們各代表了一個政治思想史上的戲劇性轉捩點。您是否能講一講是如何深入研究這些人物的?這個問題的背後是,要如何選擇在何處發掘?
關於在何處發掘的問題,我遵循極其傳統的規程。有時這點讓我感到尷尬,不過我目前為止還沒發現它過分困擾了我的閱聽人。但有時我發現自己在思考,特別是準備在中國或美國演講時,談論西歐精英文化是否仍可獲得接受?因為那是我研究的重點。我主要寫過湯瑪斯‧摩爾、莎士比亞、彌爾頓、洛克,尤其如你所說是關於馬基維利和霍布斯。不過,如果我擔憂這點,那為何仍要選擇發掘呢?我的回答並非是我特別欣賞馬基維利或霍布斯。實際上,我發現他們有些言論令人生厭。但最初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倆都如此完美地描繪出了我在思想史上想提出的、更為普遍的主張。
正如我提過的,我最想提出的主張之一是,即便是最抽象的政治哲學著作,也需要將之理解為對既有對話或辯論的介入。若想要理解,就需要確定其意圖參與的特定討論。如果這是你意欲贊同且實踐的研究取徑,那麼馬基維利就為說明其獨特優勢,提供了完美的途徑。馬基維利繼承了人文主義的假設,即政治的目標是偉大和榮耀,而達到這些目的之途徑是擁有德性(virtù)或普遍德行(virtus generalis),即智慮、正義、勇氣、節制的「樞要」美德。馬基維利在《君王論》(Il principe)中同意統治者的目標應當是偉大與榮耀,而這點需要「德性」。但馬基維利接著宣稱假設「德性」概念,可折換為一系列美德,不啻是毀滅性的錯誤。他反過來辯稱,政治領導者必須認識到的是,凡能帶來榮耀與偉大之特質就名為「德性」。這所導致的行為一直都會是美德的事例嗎?據馬基維利所言,沒有機會。因此,說得粗糙些,這就是馬基維利革命。但若想了解,則要辨別馬基維利在公認的政治道德論述中,所進行的顛覆性介入之準確類型。
馬基維利繼續在《君王論》第十八章中說,真正的政治行家(virtuoso)是了解模仿獅子與狐狸之價值的領導者;亦即,知道勇猛與狡詐,對政治成功而言不可或缺。要掌握此一關鍵主張的重要性,必須理解除了其他意義以外,這還是對西塞羅的諷刺。西塞羅在其《論義務》(De officiis)中宣稱勇猛是獅子的特質,而狡詐是狐狸的,並貶斥這兩種特性是獸性、野蠻的,因而無法與人類匹配。馬基維利說,這些正是男人要想成為成功領導者必須培養的特質。馬基維利不僅拒斥西塞羅的人文主義,而且嘲笑他的正經。回到我取材自奧斯汀的公式,這就是馬基維利在這段著名的文章中「所做的」。我想說的是,這是思想史學家應尋求的理解:一種對他們研究的作品中到底是怎麼回事的賞析、一種對作者所為的理解。簡而言之,我專注於馬基維利的最初原因之一,屬於和歷史幾乎同等的方法論:馬基維利完美說明了我想提出的某些更為普遍的主張。
您在美國,特別是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時間,如何影響了您的研究和興趣?
一九七四年,我在劍橋學術輪休的一年,就去了高等研究院。接受了偉大的西班牙近代早期史學家約翰‧艾略特(John Elliott)爵士之邀,我在高等研究院的歷史研究學院度過了這一年。但我在那裡受邀在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和克利弗德‧紀爾茲建立的社會科學學院擔任為期五年的研究員,他們已經聘請了湯瑪斯‧孔恩和威廉‧蘇沃(William Sewell)。事情的發展是,我只再待了三年,因為我和妻子都獲劍橋以誘人職位邀請回校,而決定返回家鄉。但我在普林斯頓的四年,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非常享受這段人生時期。
你問我在高等研究院的時間,如何影響了我的研究和興趣。我必須說,儘管這聽起來很自負,但這段時間並未導致我的觀點或研究風格,發生任何重大轉變。我到那裡時已然是忠實的維根斯坦主義者,而我幾乎所有純方法論和哲學的文章在那時皆已發表,其中大概有六篇出現在一九六○年代末和七○年代初。況且,紀爾茲也同樣深受維根斯坦影響,正如他在上本書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因此,我發現高等研究院的氣氛融洽,而不具挑戰性,至於我在那裡的時間,主要用來鞏固和加深已有的知識追求。
儘管如此,進入高等研究院是我一生中程度最強的學術經歷。我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比當年的劍橋更致力於研究──這毫無疑問也提升了我自己的本領──而且還有大量的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工作。我在劍橋辛苦了幾年,想對近代國家的興起進行大規模研究,但總是無法寫成。但在普林斯頓度過了三年以後,我成功寫完了這本書,並於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名為《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專著。
除了讓我能進行更多研究之外,我在普林斯頓的時光還讓我認識了一群最傑出的學者,大為提升了我的哲學和歷史興趣。給我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一位就是紀爾茲。要和紀爾茲熟悉起來不容易,因為他既靦腆又暴躁,但他成為了一位非常有價值的導師和朋友。紀爾茲是我有幸認識的最具原創力和廣為閱讀的學者之一,在文學、哲學以及廣義的人文科學中悠遊自得。身為民族誌學者,紀爾茲一直對概念如何聚集起來,藉以建構可行的生活形式充滿興趣,即使這些概念對我們而言似乎很陌生。這種方法產生了他最有力的作品之一,出版於一九八○年的《內加拉》,亦即他對所謂「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的研究。我為《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寫了該書的評論,且對其印象深刻。這是部關於國家概念的書,但在其中根本不將國家作為強制機器的名稱。藉由讓我們知道國家關乎權力,更同樣關乎展示,而展示亦可為權力之形式,紀爾茲不僅成功闡明了一種看似陌生的思考方式,也同時讓我們自問社會中權力與展示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這似乎正是思想史學者和民族誌學者該採用的方法,這無疑影響了我自己以後關於國家理論的研究。
我還要提到孔恩,他在研究院的辦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經常突然進來我的辦公室,談論他當時開始研究的意義轉變。我認識孔恩時已受到他於 一九六二年首次出版之《科學革命的結構》極大影響。孔恩的核心思想尤其使我著迷,即我們所謂的知識存在於典範之內,而直到典範本身開始受到懷疑,建立起典範的反例時,改變才會發生。同時,典範將用於消除明顯的異常,這正與卡爾‧波普關於所謂關鍵實驗之角色的主張相反。和紀爾茲一樣,孔恩也傾向於認為理性上的相信,部分取決於你另外相信之事,而非取決於能毫無爭議地稱為「證據」之事。
我還花了很多時間與普林斯頓大學中,兩位領路的哲學家前輩理查‧羅逖(Richard Rorty)和雷蒙‧葛斯(Raymond Geuss)往來並從中獲益。羅逖當時寫的是《哲學與自然之鏡》(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於一九七九年出版。我在《紐約書評》中也十分讚揚該書。羅逖將他對維根斯坦、奎因(W. V. Quine)與孔恩之分析,大膽地推向相對主義的方向,這令我特別驚訝,我還與他對思想史家致力於某種形式之概念相對主義的程度,進行了廣泛討論,無論是在出版文章中還是在對話中。我和後來在劍橋成為同事的葛斯共度的時間更長,而我正是從他那裡學到了將系譜學視為思想史家使用的工具。葛斯原來主要對尼采的意見感興趣,亦即追尋我們信仰起源之行為足以貶低信仰。我最終也許更維根斯坦主義一些,僅將系譜學作為有用的工具,用來追溯如何個體化與定義概念上經常出現的爭議。大半是與葛斯的討論促使了我撰寫後來發表的關於自由與國家概念之系譜研究。
在您的《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您複雜化並挑戰了賦予文藝復興時期新穎性的某些觀點──特別是藉由表明古典共和主義等觀念具有更深遠的中世紀淵源。您如何理解觀念史中變化與連續性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近代早期的時段?
你說得不錯,我的目標之一是挑戰近代早期歷史的傳統分期。當然,常用的標籤確實無法輕易擺脫,而在書名中避免背叛自我尤為困難。《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第一卷標題為《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確實特別符合常規。但我不僅是意圖喚起,並且是要解構十五世紀佛羅倫斯所出現的獨特文明之布克哈特式(Burckhardtian)意象。在我寫作的時候,這種思維仍十分普遍,不僅構成了漢斯‧巴倫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早期的危機》(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甚至構成了約翰‧波考克在一九七五年的傑作《馬基維利時刻》(Machiavellian Moment)。而我反過來試著回到十二和十三世紀有關羅馬法律與政治思想中「最高權力」(suprema potestas)的辯論中,追溯義大利城邦國家共和自治理論與實踐的出現。
《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第二卷名為《宗教改革》(The Age of Reformation)。我在其中想質疑的論點是:如邁克爾‧瓦爾澤(Michael Walzer)和朱利安‧富蘭克林頗具影響力地提出的,近代憲政主義詞彙的具體化是新教改革的獨特遺產之一。我試圖證明的是,賦權、有限政府及以政治抵抗權等相關理論的發展,皆與對天主教會固有組織的長期辯論有所關聯。法蘭西斯‧奧克利(Francis Oakley)已開始用類似詞彙進行討論,但我在此主要受惠於梅特蘭(F. W. Maitland)出色的學生菲吉斯(J. N. Figgis)的作品,他在《從葛森到格勞秀斯》(From Gerson to Grotius)中,證明了關於教會會議至上主義(conciliarism)之辯論,對近代世俗國家形成產生的深遠影響。
您先前提到過漢斯‧巴倫。您是否也曾回頭重讀了他與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的辯論?
我一直都支持克里斯特勒的立場,後來與別人合編《劍橋文藝復興哲學史》時,我為自己說服克里斯特勒撰寫關於人文主義的一章而感到十分自豪。我認為最好將「人文主義」理解為課程名稱是克里斯特勒的基本主張,而我深受其影響。克里斯特勒不僅清除了很多有關文藝復興時期發明了所謂人文價值的浪漫廢話,還證明了「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主要源於羅馬而非希臘,而重新錨定了歷史書寫的方向。正如克里斯特勒所展示的,課程包括五個要素:文法(對拉丁語的研究),其次是邏輯和修辭,然後是歷史和道德哲學的研究。西塞羅成為了中心人物,是修辭理論與實踐的專家,以及有影響力的道德與政治建言提供者。克里斯特勒展示出義大利王國(Regnum Italicum)早在十三世紀,便發展出一種基本是西塞羅式的修辭文化,其最終在十六世紀導引出馬基維利和圭恰迪尼與歐洲北部的伊拉斯莫斯與摩爾所寫的這類歷史與政治建言書。儘管克里斯特勒總是謹慎而謙遜地提出自己的發現,但其影響是提出了一種從事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政治理論的新方法,這部分略過了所謂經院主義(Scholasticism)的影響,並連結了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初這整個時期。
您長期以來一直對修辭學(ars rhetorica)和修辭學的歷史遺產感興趣,在您最近的《庭辯中的莎士比亞》(Forensic Shakespeare)中達到頂點。最早引起您對古代修辭傳統遺產興趣的是什麼,而其如何影響您思想史及政治思想史的方法?
我對修辭學的興趣最早是由閱讀克里斯特勒引起的,但也受傑洛德‧西格爾(Jerrold Seigel)於一九六八年出版的開創性著作《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修辭學與哲學》(Rhetoric and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Humanism)影響。上述作品驅策我回頭去讀西塞羅,我在中學時學習過西塞羅部分演講的內容。而我現在轉向西塞羅關於演說的理論性著作,尤其是《論雄辯》(De oratore)。我在其中見到了西塞羅對兩類論述的關鍵區分,其一特徵為科學,另一特徵則由西塞羅標誌為人文科學。西塞羅認為,諸如文法或數學之類的科學,可以完全仰賴理性(ratio)提供證據作為力量。但在人文科學中,若我們要成功提出自己的論據,則還需依靠說服力,因此也需要雄辯(oratio)或演說的力量。換句話說,就如同西塞羅所云,人文科學的特點是問題總有兩面的事實,因此我們便總能希望在兩個方面(in utramque partem),即在任何一方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述。
因此,對西塞羅而言,人文科學──包括法律與政治──當中論述的原理必須由修辭開題(inventio)理論提供,即西塞羅在《論開題》(De inventione)一書中概述之理論。精通「開題」讓我們能發現(invenire)不同情況下,最有說服力的推理類型,並向我們展示如何以最佳順序和最有力的「雄辯」與「理性」組合安排論述。我認為,我們現今傾向僅將修辭等同於言語修飾(詞藻),尤其是藉由修辭手法所進行的言語修飾。但對西塞羅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修辭教育傳統而言,這是種獨特而不可或缺的論辯藝術之名。
你問如此理解的修辭學研究,如何形塑了我身為思想史家的工作?我的回答是,這是我兩部專論的核心。一部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霍布斯哲學中的理性與修辭》(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霍布斯在其最早的政治理論著作《法律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Law)發表之初就指出,他的目的是要採取另一方將無處容納論述的方式來闡明政治原則。這同時是對西塞羅之人文科學解釋觀的引用與否定,而我試圖探索其重要性。我特別試圖追溯霍布斯對修辭藝術的反感,以此作為解釋《法律的要素》,與其一六四二年出版之《論公民》(De cive)結構的手段。然後,我將該方法對照霍布斯在《利維坦》結論中爾後的讓步,即若要建構政治學的任何前景,理性和雄辯必須「站在一起」。我試圖證明這種與修辭藝術的融洽,如何影響了霍布斯對公民科學的成熟演示,引領霍布斯展開更廣泛的論述,特別是採用諷刺與嘲弄的修辭手法與對手往來。
我以修辭學理論為主題的另一本書是《庭辯中的莎士比亞》,於二○一四年問世。我應該解釋一下,對許多我這一代的英國人來說,莎士比亞是教育的中心人物,我們深入研究了他的許多戲劇。在寫關於霍布斯投入修辭藝術之改變的著作時,我不禁注意到,修辭手冊的作者提出的大多數建議,在幾部我熟知的莎士比亞戲劇的語言與結構中似乎有所呼應。不過,若我未曾受邀參加二○一一年在牛津舉行的克拉倫登文學講座(Clarendon Lectures in Literature),我認為我不會有信心去探索這些直覺。我以「莎士比亞與修辭發明」為題發表了一系列演講。我試圖展示,在一組最重要的《哈姆雷特》與《奧賽羅》的莎士比亞中期戲劇中,運用了古典修辭技巧進行兩方論辯,而以此為中心組織了許多關鍵演說和場景。
您能告訴我們您的研究方法嗎?您如何開始一項計畫以及如何寫作?
我曾經讀過一部文集,其中多位學者確切解釋了他們開始研究特定主題,以及最後坐下來寫作時所發生之事。我發現這些故事引人入勝,但也為之困惑,因為我意識到我沒有這類故事能講。我真的不太清楚我是怎麼做的。我知道我會速記下很多筆記,然後對這些筆記做一些更系統的筆記,並在過程中試著讓這些筆記形成草稿。接著我曾習慣於將草稿進行打字,不過自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來,我和其他人一樣都用電腦。而且,和其他人一樣,這意味著我現今可能寫的比我所應寫的還多。
然而,我已經認識到了,我在很長時間以來都遵循結構性原則在做筆記。我在所研究的文本中,看到讓我想起其他文本的東西,我便開始將這兩個文本並置對比。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例如:我在寫關於安布羅喬‧洛倫采蒂名為《好政府》(Buon Governoro)之壁畫系列的文章時便是如此。我注意到,該系列的規畫取材自許多早期人文主義者的政治論文,特別是布魯內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關於市政廳的短論。我得出的研究中先闡釋該部關於暴政與德治的文獻,接著試著展示洛倫采蒂傑作中的細節,大多可參照該文本來解釋。
為莎士比亞的庭辯劇本做筆記時,我遵循了相同的原則。我注意到,正如我所言,莎士比亞在其中一組戲劇中,將修辭規則廣泛用於司法目的。因此,我的書首先講述了羅馬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司法理論,然後試著說明這些規則在每部相關劇作中的應用(有時則是反抗)。這種方法本質上是柯靈烏式的,優點在於論辯易於理解。但缺點是存在片面辯護的危險;另一點是,書的設計是為了辨別介入並解釋難題,以至於組織得有些機械。我還是覺得我的方法優點大於缺點,但部分批評者並不同意。
雖然並置對比一直是我主要的學術技巧──如果能描述得如此宏大──我也必須承認敘事閉合的弱點。在我的《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我主要志在追溯主權國家的近代概念,如何從各種司法轄區與政權的中世紀背景當中產生的過程。在政治作家開始評論結果亦且描述他們所獲之「國家」(lo stato)、「國家」(l'état),或者說「國家」(the state)總體概念的時刻,我結束了這本書。我認為這種結局令人滿意,儘管後來我受到譴責──恐怕這不太公平──因為我用宏大敘事來代替許多本來可以說的矛盾故事。我在二○○八年出版的《霍布斯與共和主義自由》一書中的寫作方法類似──但我想我成功地避免了批評。我追溯了個人自由相關的思考方式演變,其中認為自由的反義詞是依從他人的任意意志。我試圖表明霍布斯是如何質疑此一分析,並劃時代地成功將觀點改換為自由存在的唯一標誌,便是外部約束不存在。我在這種新的自由觀成功挑戰了既定觀點時,結束了敘事,將後者導致的霸權喪失作為另一種結局形式。
研究和寫作是私人過程,或者您在進行研究計畫時會與他人談論?
對我而言,這個過程最好完全是私人的。我從不喜歡在投入研究時談論我的研究。我在普林斯頓的那幾年中發現這很困難,因為在我看來,大多數人總是想討論他們的學術計畫。這裡可能存在文化差異,因為我從小到大都相信談論自己是不良習慣。但我認為我的不同主要源於害怕,如果我與專家談論正在思考的主題,只會發現自己偏離路線,或受他人的評論和批評而感到挫折。我寧願等到完成再說,在這一階段,我非常渴望將自己的作品給專家看,期望得知當中是否有誤。回應有時可能令人沮喪,但我總能發現它們帶來了改善,某些情況下,我獲得的幫助數量,幾乎令人頗難為情。
您先前提到,您還留著某些學生時代的書,上面留有筆記。您如何與您的私人藏書互動?您會在書上寫筆記嗎?
我想,就如同我這代所有學者一樣,我有個巨大的私人圖書館,而我一直僅將我的書視為工具,在空白邊緣處塗寫,並在文字底下畫一堆線。但資料庫的可用性改變了我的學術生活。當然,我討論的某些作家總是一致的──最明顯的是西塞羅、彌爾頓與莎士比亞。但現今能下載大量可搜尋的文本,導致思想史的學術標準已上升到從前難以想像的高度。我剛起步時,必須像基斯‧湯瑪斯才得以(因為讀過所有內容)說出諸如「直到Y時才出現X 詞」的話。但如今在線上檢索一小時左右之後,任何人都能以同樣驚人的精確度講話。
推薦序文
思想史於一九八○年時本已被視為行將就木。法國史學者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在一份關於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考察中指出,這個領域已經失去了那曾使它充滿活力的火花。在一九八○年之前的二十年中,法國年鑑學派的社會史在大西洋兩岸贏得眾多追隨者,而且量化方法被視為是歷史探究的至高守則。同時,受人類學的影響,新的研究方向轉向了大眾文化的研究。在許多人看來,觀念史──這個亞瑟‧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在一九三○年代所開創的領域──似乎已是往昔的遺跡。當時有誰能預料到,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思想史──針對過去人們思考和求知的成果之研究──會成為歷史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之一?
事實上,即使在社會史的鼎盛時期,某些學者仍以一種反主流文化的態度,繼續研究思想活動的歷史。而且他們尋求新的追索方式,無論是通過科學史、人文學,還是政治思想。此後,思想史在文化史寫作熱潮的背景下推陳出新,這種轉變已有不少研究以及頌揚。歷史學家經常將這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的變化,概念化為「轉向」(turn)。然而,一個整體性的文化轉向概念,並不能充分解釋思想史的復興,因為思想史的譜系要比文化轉向更為多樣,也更為悠久。它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中葉豐富的學術成果,而當時這些成果同樣也在與更早期的學術成果對話。思想史的再次崛起並不是平白無故的,正好相反,思想史在過去幾十年中的東山再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重新振興自身舊傳統,而且這種振興甚至在社會史擅場時便已在進行。
思想史不再被視為落伍,或甚至是食古不化;相反地,愈來愈多懷抱壯志的青壯年學者被思想史所吸引,並且發表了大量創新性著作。這個領域有了愈來愈多的期刊和學術協會,它的現狀和前景在最近引起了一些反省。來自不同領域的洞見,如科學史、書籍史、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和物質文化的研究都豐富了這個領域。「觀念」的歷史在此過程中轉變為「思想」的歷史。思想史不再將抽象事物視為理所當然的研究對象,它開始將思想的運作視為人類活動的一種形式,其代價和成果不只會展現在思想上,也會呈現在個人、政治和社會等各層次上。它不再僅僅將思想歸於孤獨的哲學家或學者,即「天才」,它也不把它們限縮在菁英文化的範圍內。像是「西方」這種涵括範圍極廣的同質性分類,以及對傳統、正典和古典的簡化性概念,都已經變得更加複雜、微妙和異質性。但是,如果對思想活動的研究不再擁抱這些古老的真理,那麼思想活動現在是由什麼構成的呢?思想活動的研究者又該如何定義他們現在的這門學問呢?僅僅將過去過分簡化的敘述複雜化就足夠了嗎?應該用什麼(如果有答案的話)取而代之?
《面向過去思考:與史學大師的爐邊閒談,打造歷史思惟的八場對話》提供了對這些問題的一系列反思。本書採訪了八位歷史學家,其中一些人從一九六○年代或一九七○年代起就很活躍,另一些人則是較為晚近才奠定了學術聲望。於二○一四至二○一七年期間,在柏林、馬薩諸塞州劍橋、倫敦、紐約、巴黎和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進行的非正式談話中,這些學者揭示了他們如何來確立在思想研究上的目標、他們如何進行研究,以及他們對此領域未來之展望。在當代學術界,無論是學科系譜還是這門學問的奧秘,基本上都是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除了私下交談外,歷史學家一般不會談論這些話題。我們希望通過出版這些訪談,將歷史學的「隱秘科學」公諸於世。換句話說,我們希望本書是自己還是思想史研究生一年級時,能夠讀到的一本書。這樣的書尚未問世,所以我們必須自己把它寫出來。
採訪形式對於揭開歷史學家技藝的神秘面紗,以及勾勒出晚近歷史著作的粗略圖像,這兩個層面都是相當理想的。這本書可以說在兩種意義上是與實踐(practice)有關。首先,它不僅揭開了思想史研究和寫作的面紗,並且探討了思想史家是如何從實踐的歷史看待自身的研究。我們的受訪者努力重建早期、其他思想者的著述。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種對實踐的強調並不意味著,套用另外一個時代的用語,外在主義方法凌駕於內在主義方法之上;相反,我們採訪的歷史學家一致認為,內在與外在那曾經喧囂一時的對抗,都已被封存在過往之中了。內容和脈絡已不再相互排斥,今日的思想史家必須兩者兼顧,他們必須關注研究對象的政治和社會背景,同時不忽視其思想內容,無論它可能有多麼的專門或是晦澀。
我們選擇受訪者的方式當然是武斷的,但是我們謹遵要編寫出一本清晰易讀書籍的要求。我們本來希望進行更多的對話,遠遠超出本書的篇幅範圍。不過,正如本書最終的完成樣貌所示,我們選擇了代表思想史不同分支的歷史學家們:書籍史(安‧布萊爾[Ann M. Blair]);科學史(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非西方知識傳統的歷史(班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學術史(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哲學史(吉爾‧克雷耶[Jill Kraye);古物學和物質文化的歷史(彼得‧米勒[Peter N. Miller]);宗教史(讓-路易‧貢當[Jean-Louis Quantin]);以及政治思想史(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採訪者的順序是按照英文姓氏字母。)
八位截然不同的人回顧他們的人生與和職業生涯,要對這些內容一概而論十分不容易。然而,這些對話確實揭示出在提出問題上,常見的一些模式或偏好。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受訪者敘述的是他們漸進地重構既有觀點的的過程,而不是戲劇性的逆轉。而且,他們在訪問中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們,要對他們自己用回憶來重建持保留態度。各種形式的歷史記憶都可能是脆弱的。然而,我們的學者講述了他們如何從過去的思想遺產中來幫助自己,解決感興趣的問題,這些遺產令人驚訝地相當多元而且深入。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講述了偶然相遇──與師長、同事和書籍的緣分──如何意外地塑造了他們的智力發展。此外,這些回憶與他們當中好幾位書寫思想史的方式一致:這是一個與現有思想資源進行拉鋸協商的複雜過程,而不是一連串靈光一現的時刻和扭轉視野的宣言。
我們的取徑是將思想史本身視為一門專業,而不僅僅是文化史中的一個分支。思想史並非文化史的子領域或子類別。正如我們的受訪者強調的那樣,思想史現在不僅包括書面文件,還包括建築、藝術、自然知識、文學、音樂、宗教和儀式──總而言之,所有人類文化的產物。然而,思想史和文化史之間的區別不僅僅是語義上的區別。思想史是以一套方法和技巧來定義自身,而不是依靠史料來源。思想史強調思想、知識和資訊,以及對世界的解釋,它是研究文化中各種面向的一種獨特模式,無論是文本、儀式或是物質對象。
注重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使歷史思維和實踐中一些重要而又被忽視的變化,其輪廓更加清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思想史在方法論上尤其富有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學者們擴大了思想史的史料範圍。史金納對安布羅喬‧洛倫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的壁畫和莎士比亞戲劇的研究展現出,政治思想史的領域應該遠超過一般認定的小冊子或專著。涵蓋範圍的擴大還包括了去關注一些更遠離傳統的層面,特別是在學術論文不是知識生產之主流的那些時期。正如克雷耶所說:「哲學史中間從不存在任何空白。」她和其他學者深入研究了被遺忘的文體,例如:附上批評的新版本和評論。近代早期歐洲,在文藝復興和之後古典學復興的人文學者,寫一部獨立的專著或敘事史是相當罕見的。相反,許多人文學者對已經存在的文本,尤其是古代文本進行了注釋,發行新版本和翻譯。這些作品,通常被認為是次要或衍生的,以前被思想史學家所忽視,他們也因此忽略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絕大部分的作品。評論和新版本(作為對已有文本的回應和重構)這些可能貌似不具革命性的文件,然而為作者提供了很大自由空間來討論棘手的問題,包括文本權威、歷史批評和宗教啟示。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斯之所以引起轟動,不是因為他寫了一篇要破除《新約聖經》當中偶像崇拜的論文,而是因為他編纂了一本新版本的《新約聖經》,其中他悄悄地刪除了約翰福音的一段他認為是虛假的經文,該經文便是聖經中支撐三位一體教義的關鍵段落。對於編輯、注釋、批評和評論等等傳統的挖掘,後來的發展不僅證明了其實用性,而且對於想要去理解那些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個別獨立作品的現代讀者而言,這些挖掘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背景膠帶,從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對《君士坦丁的捐贈》(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攻擊到湯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
就中國的傳統而言,科舉的應試論文作為一種可以運用,但長期被忽視的資料,在艾爾曼的研究中被證明,其有力地反映出中國精英階層對地緣政治的關注。對於格拉夫頓來說,歷史編年學這門現在已經不存在的學科,其主要以評論形式呈現的成果,則提供了我們一個窗口,讓我們得以明瞭近代早期學者如何權衡證據、比較傳統,並試圖調和歷史資料與宗教信仰。達斯頓通過一些出乎意料的具體物體和文學類型,來探索諸如合理性和客觀性等抽象觀念的歷史,無論是奇物收藏、植物學插圖,還是較為近代的中世紀烹飪書和禁奢法。
此外,當前的思想史研究者還試圖重建科學和人文知識在特定時刻的物質、制度和文化背景。布萊爾追溯了近代早期百科全書和參考著作的急速增長,並且解釋是這其實是對於印刷技術興起所引發的「資訊超載」感(information overload)的回應。克雷耶則清楚地指出,若要掌握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史,就必須要理解大學課程中的亞里斯多德傳統;要理解像笛卡兒(René Descartes)這樣的人物,我們必須詳細復原他在學生時代於課堂學習到的東西,即使他表現得出十分排斥這樣子的訓練。歷史學家也愈來愈重視體裁、語域(register)、修辭和思想上的自我塑造。史金納重建了羅馬修辭傳統(ars rhetorica)的漫長影響力,並且證明直到近代早期都一直是種活躍強健的論述,從政治到戲劇在內的所有領域都對其加以運用。貢當探討了教會史的這個體裁,與文明或世俗史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它的主題,而且在於其方法,因為它的寫作目的往往是要裁決神學家之間的神學爭論。
類似地,思想史家逐漸地更加重視學者的工作方法,還有知識分子社群及其網絡的影響力上頭。布萊爾目前對於書記(amanuenses)和「隱匿助手」(hidden helper)的研究,清楚呈現了知識生產當中的的合作面向,而這種合作在許多時候(而且是故意)被早期敘事中那群孤獨天才的作者自身所掩藏起來。米勒重建了一位十七世紀的知識分子,法國古物學家尼古拉斯-克勞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儘管他沒有出版自己的作品)是如何與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和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這些著名人物保持著大量的書信往來,他同時還與無數的商人維持通信,這些商人的足跡遍布地中海和黎凡特(Levant),儘管他們現在已被遺忘。艾爾曼的考生、格拉夫頓的編史者、貢當的神學家,布萊爾的抄寫員和米勒的古物學家,都不是人們在過去思想史研究中會見到的典型人物。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在努力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過去。一旦書籍、思想、甚至學科不再被視為思想史的創新前沿,它們在出現後持續存在的漫長壽命又該如何被解釋?只要歷史學家只去關注「各方面首先出現的人事物」的一天,他們就無法理解教科書中那些被視為連續,但其實是彼此交錯的不同知識傳統。就像布萊爾挑釁地提問:「我們何不看看那些『較遲出現的人事物』?」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還是十七世紀的經院哲學爭論,那些曾被認為行將就木的知識傳統後來的長久存在,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如何書寫思想史的宏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事實上,用從頭重寫人類思想史這種超越逐步累積的方式來理解所有這些新貢獻,是一項仍在進行中的計畫,我們希望本書記錄的對話,日後將會被證明具有啟發性意義。
這些修訂和重新概念化已經在許多領域出現。隨著新活力和相類方法紛紛出現,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已經在許多不同的研究領域獲取了一席之地。僅舉幾例,包括晚期古代的地中海和近東、伊斯蘭思想史、南亞的文學傳統、現代西方哲學,以及科學史的許多分支。這些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在處理其材料時,他們的目的和目標都與本書所探討到的領域相似,因此前者的研究方法的起源同樣值得研究。事實上,我們希望這些領域和其他許多領域的學者,能夠針對自己的知識實踐製作口述歷史。
然而,從上面列出的受訪者可以清楚看出,本書中收錄的歷史學家所研究的時代,大約都是在一四○○年到一八○○年之間。這種刻意的強調確實是按照我們私心所做出的決定,它反映了我們根據自己的專業領域和專長作出的選擇。但它也顯示了一種特別的活力,其激發了所謂近代早期的數個世紀的研究蓬勃發展。過去幾十年中一些最具影響力的史學發展,便是出自近代早期這個領域,這些史學發展的影響力很清楚地已經遠遠超出近代早期的範疇。僅舉幾例,其中包括政治思想史、新的古典學術史、科學革命敘事的改寫、宗教和信仰研究的新方法、微觀史作為一種類型的興起,以及書籍史和閱讀史的誕生。
為什麼近代早期這時代,正如人們所知,會對晚近的學術研究有如此顯著的影響?這些採訪的目的之一便是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其中有三個主要的主題。
首先,就其本身而言,近代早期無疑是一個巨幅變革的時代:這時期發生了宗教的重建和變革、全球人群往來的增加,以及新的技術和科學追求。在二十世紀初期,法國學者保羅‧哈扎德(Paul Hazard)認為,印刷、古典復興、美洲的發現和新哲學這四項創新,在歐洲帶來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並刺激出他所謂「歐洲思想危機」。在不否認這些發展的變革性質的前提下,我們要強調的是,近代早期這時期也不僅是在歐洲,也包括其他知識傳統中的人們,尋求過去的借鑑來理解他們眼前那不斷變化的世界。知識傳統與變革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所有時代的歷史背景下均存在,但在十五至十八世紀之間尤為明顯。在這幾個世紀當中,希臘羅馬的過去、早期基督教和原始教會的願景、中國的古典傳統、伊斯蘭的古典傳統這些繼承下來的知識文化,似乎仍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創新往往被框定為革新或復興。後來,西方現代性的論述將致命地削弱傳統知識文化的權威性,這不僅出現在歐洲,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因此,近代早期的思想史,由於堅守過去權威的態度,與新的現實和知識之可能性所帶來的挑戰,兩者之間在思想上所激發的碰撞,使這段歷史至今仍然歷久不衰並且發人深省。
因此,對於我們現代學者而言,近代早期宛如一個實驗室,讓我們可以審視新的思想、實踐、技術和制度如何與非常古老的思想、實踐、技術和制度共存和衝突,後者包括那些從遙遠過去繼承下來的、被近代早期人們稱為「古代」的思想和制度我們的受訪者都指出,創新的達成往往是藉由恢復過去的某些面向,而不是徹底否定過去。變化和連續性並不是簡單的對立,而是人與自己在思想上的繼承之間,不斷重新發現和拉鋸拔河過程中的複雜內容。這也向歷史學家提出了難題。例如:在近代早期的歐洲,下列何者應該被更加重視:一直到十八世紀都依然存在著,擁有悠久歷史的經院哲學,還是首先由人文學,後來以新哲學所代表的斷裂?是要更重視印刷術發明帶來的革新,還是與中世紀手稿文化一路傳承下來,在書寫和閱讀的諸多特點?是要強調新發現的古典文本中看似陌生的面向,或者要注重這些文本在哪些層次上,可以為既有的習俗和規範辯護?
其次,借鏡近代早期來「思考」富有用處的另一個原因是,那幾個世紀當中知識文化的流動性。這時代的知識分子從事著寫詩、收集古物、研究天文學與語文學、鑽研錢幣學與金石學等各式工作。阻礙我們前進的界限和區別並不存在於他們當時的視界中。我們現代歷史學家拓展自我視野的方式,以及所要面對的挑戰,便在於如何完整恢復過去知識分子所會觸及的思想視界。回顧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出現學科劃分之前的時代,對於質疑是什麼構成了知識傳統或一門學科,甚至是一組學科(如人文學科),以及探索科學和人文兩種文化之間被預設存在的區別,都是可以帶來豐碩成果的。換句話說,接連不斷的改變是饒富生產力的。
第三,近代早期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起源系譜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近代早期這名稱即表現出一種目的論,還有要將其所指的事物與現代性區別開來的需求。無論如何矛盾,我們仍然在從近代早期傳統中學習,既學習如何去衡量我們與近代早期人們帶來的世界之間的距離,也學習該如何確定現代性本身的序幕或預兆何時出現。這種矛盾性清楚體現在目前仍在進行的辯論中,即「我們」這群二十一世紀的人,究竟在多少的程度上,可說是文藝復興時期、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繼承者(好壞與否則是另一個可以辯論的主題)。近代早期在某種意義上已是近代,但也尚未完全進入近代,因此我們所關注這個時代的思想產物的特色,是一種既靠近,同時又保持距離的作法。正因為近代早期在理解現代與過去關係上,占據了獨特的位置,它成為了思索知識傳統和歷史變遷本質的絕佳領域。
當我們開始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對於受訪者可能觸及的主題有一些大致上的預期答案。然而,許多其他主題在我們沒有提示的情況下出現,我們因此經常在採訪之間遇到意想不到的呼應和共鳴。某些在思想上的啟迪,例如: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也許並不令人感到驚訝。與瓦堡圖書館相關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特別是其創始人阿比‧瓦堡(Aby Warburg)對於古代在文藝復興文化中如何再生的研究。約翰‧波考克(John G. A. Pocock)的作品,特別是他在一九五七年的著作《古代憲法和封建法》(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是將我們所訪問的歷史學家們串連起來的最有力的線索之一,特別是出自於這本書針對近代早期世界中歷史書寫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受訪者的研究也是奠基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思想史與文類、慣用主題(topoi)的綜合研究上頭;而這種綜合研究又是承自研究中世紀的學者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和恩斯特‧羅伯特‧柯蒂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傳統,他們兩人是比較文學發展為一門專業學科的重要人物。卡爾‧休斯克(Carl Schorske)後來囊括了音樂學到精神分析學的折衷文化史(eclectic cultural history),,也是多位史學家的重要靈感來源。與此同時,義大利古典主義學者阿納爾多‧莫米格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將古典研究與對古典傳統在古典結束後的發展探究相結合,成為學術研究史上的一種典範。達斯頓早期的研究明顯受到伊恩‧哈金(Ian Hacking)著作的影響。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史上,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的影響力顯得尤為突出。還有另一個關係更為遙遠的領域:人類學家克利福德‧蓋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著作影響了我們兩位在一九七○年代已經十分活躍的受訪者──史金納和格拉夫頓。綜上所述,我們的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的靈感與知識來源遠遠超出了歷史學科和近代早期研究的範疇。
其他共同點還包括強調合作研究的重要性、確立作者真作目錄的困難,以及做出要從何處展開計畫的的挑戰性。「相信你的嗅覺」是個一直被反覆用來解釋歷史探索問題過程的隱喻。它鼓勵人們在尚未可以說清楚自己的興趣是什麼的時候,就展開行動。事實上,我們的許多從業者都回憶說,他們在學術或專業上冒過不小的風險,例如:改變主題甚至研究領域,或者在自己還不具備完成研究計畫所需的所有技術能力的情況下,就決定開始執行計畫。
這群彼此相當不同的受訪者,是被以我們所謂的選擇性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聯繫起來的。儘管他們所處理的史料性質差異甚大,但在我們採訪的學者中,不少人有著共同關懷的主題。我們將在這裡聚焦其中三個主題。首先,許多受訪者談到了近代早期歐洲文化中,古典歷史遺產的不同面向。被稱為人文學運動的文藝復興運動,恢復了拉丁和希臘的古典文學遺產,長期以來在關於近代早期思想生活的宏大敘事中,都被視為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曾經是一種勝利者的後設敘事:人文學者使用批判語言學的新方法恢復經典,一般認為這些經典在所謂的中世紀期間完全被忽視。而且,人文學者在復興了古代之後,同時是打造出現代性的共同推手;至少在一直將古代所傳下的著作視為權威的那種文化,尚未被新哲學的理性主義取代前都是如此。最近的學術研究(包括我們採訪的幾位學者)不僅挑戰了這種敘述的目的論性質,而且對它所預設的近代早期學術方法提出了挑戰。最近的研究也指明,人文學並不是在舞台上發光發熱之後就銷聲匿跡;相反地,人文學一直影響著歐洲菁英的文化觀,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甚至是更為晚近的時代。無論是歐洲的拉丁古代(Latin antiquity)傳統,還是東亞的中國古典學科,某些傳統的強大延續性便提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即當一個詞彙、流派或學科跨越幾個世紀的時候,其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其次,我們許多歷史學家對知識創造的關注程度與對思想一樣。針對知識所提出的問題既透露出科學史的影響,也透露出了人文學學術史(最近有時被稱為人文學歷史)的影響。歷史學家不僅研究新知識與新思想之間的相互作用,還試圖界定清楚新知識是如何產生,以及新知識如何從一個領域被轉換到另一個領域,例如:從口頭領域到書寫領域,或者從工匠的實驗室到理論性的論文。的確,現在人們逐漸正視工藝者作為知識創造者的身分,因為關於近代早期知識生產的新研究,已經消除了有知識者與無知識者之間那條清晰的界線。
第三,在我們訪問的學者中,好幾位都強調要克服對個別思想家的英雄化敘述,藉此來還原知識分子與其所能接觸到的知識傳統,兩者之間實際互動的多重性。綜上所述,他們對歷史的修正,是針對被篡改的歷史敘述的一劑解藥,因為後者這種敘述經常是圍繞著孤獨的知識巨人及其革新來開展。這些學者不因為某些說法乍聽之下十分新穎就照單全收,他們仔細且無情地審視過去知識分子所講述的那些關於自己的故事。在一個仍舊拘泥於偉大思想家的形象及其成就的時代,這種形式的探究不啻為思想史,更宏觀地說便是思想傳統如何演變和茁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野。
我們強調這些趨同性,並不是要低估受訪者之間的差異,也不是要把他們歸入一個單一的「學派」。思想史像是一座巨大的帳篷。截然不同的問題將我們的學者引向了不同類型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又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們無意模糊這些區別,但我們也不覺得這些區別是種麻煩。分工合作以及在方法論上的折衷主義給我們所有人的印象都是正面──不僅對學術是健康的,而且是令人嚮往的。
這些主要是關於歐洲思想史的討論又揭示了另一個問題,即歐洲歷史研究的未來。在這個全球思想史研究方法開始成為現實的時代,歐洲歷史在美國大學課程──和全球性研究計畫──中的未來仍在飄搖不定。即使書中採訪的歷史學家歡迎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過去,他們也不希望看到歐洲思想史衰落,因為這始終是成果豐碩和長期發展的研究領域。艾爾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全世界的思想史都正面臨著各種挑戰。與此同時,愈來愈多的研究(包括我們採訪對象的一些作品)探討了早期現代性本身的全球面向。近代早期的一個特徵是歐洲文化和非歐洲文化之間前所未有的互動,而這些互動本身也改變了歐洲和非歐洲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各自的過去。我們不能再孤立地研究歐洲思想傳統。近代早期研究的相關成果已經證明,這是對不同知識實踐和傳統進行聯繫和比較研究的絕佳時期。我們希望這本書有助於定義和推進全球性智識和學術傳統研究,這一龐大而亟待完成的研究目標。
與此同時,新一代的思想史家正在開拓自己前方的道路。目前的思想史研究是建立在本書受訪者在方法論上的創見,我們希望未來的研究亦能繼續啟發下一代學者。這一切研究最終會走向何方?任何概括化約的說法都是過分簡化的,而且也都還言之過早。用達斯頓在後面採訪中的話來說:關注這個領域,五年之後再來觀察其發展成果。
NT$297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