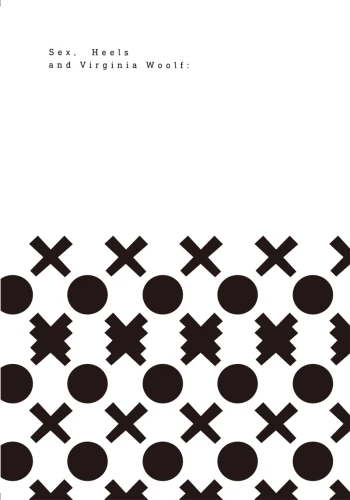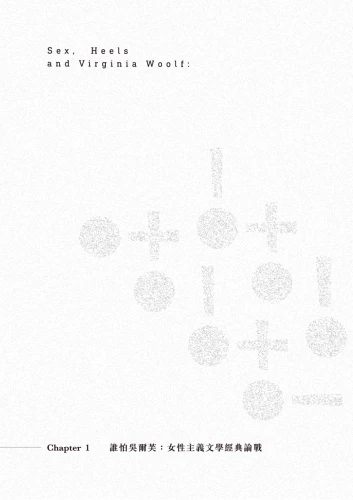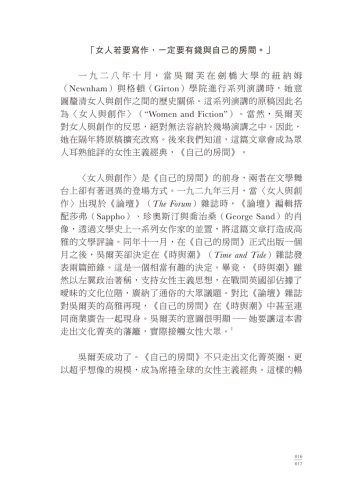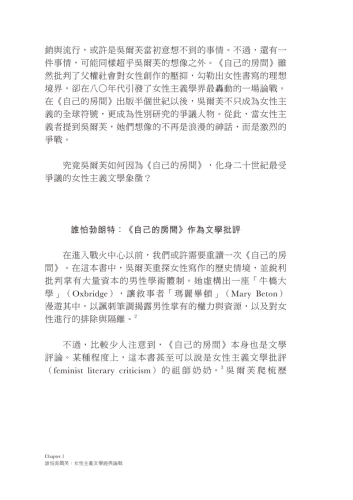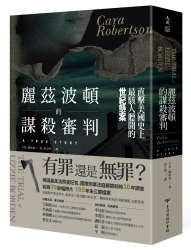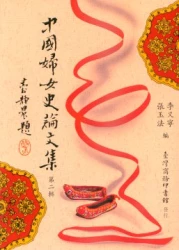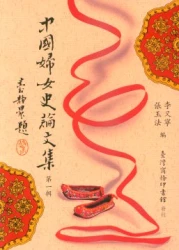性、高跟鞋與吳爾芙:一部女性主義論戰史
商品編號:04030021
定價: 350 元
優惠活動
購買提醒
本商品為出版已久的書,出版已久的書容易產生些許的黃斑、或有些許瑕疵(例如:壓痕、褪色等),不影響內文閱讀。每本書況不盡相同,請考慮評估後再購買結帳,採取隨機出貨。
如想進一步了解書況詳情,可以來信 cptw1897@gmail.com ,或點擊右上角「 客服 」留言詢問,感謝您支持臺灣商務印書館。
內容簡介
女性主義者最大的紛爭,為何總來自自己?
從性論戰、文學論戰到文化論戰,
重新召喚被遺忘的歷史爭議,
重新挖掘被掩埋的歷史衝突。
綜觀文學經典、社會運動與流行文化,
重新定義二十世紀的女性主義另翼史。
橫跨六〇到九〇年代,重探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脈絡,
以論戰串起一部歷史,女性主義者為何而爭,為何而戰?
«從珍奧斯汀到吳爾芙,女性主義者的文學詮釋戰爭
被視為女性主義先驅的吳爾芙,如何因為《自己的房間》引發文學界的世紀論戰?
珍奧斯汀如何掀起女性主義的思想之戰?「酷兒珍奧斯汀」又如何成為經典文學的逃逸路線?
«從金賽性學到女同志S/M,情慾研究的崛起引發女性主義性論戰
金賽研究團隊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人類女性性行為》,如何被女性主義者挪用為解構父權的武器?
一九八二年在紐約巴納德學院舉行的一場「性會議」,為何引爆女性主義史上最激烈的「性論戰」?
«從時尚到羅曼史,通俗文化開闢女性主義新戰場
- 時尚為何一度是女性主義者不能提及的F-Word?
- 羅曼史如何從洗腦女性大眾的「讀/毒物」,一舉翻身為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的顯學?
- 所謂的「男性凝視」又如何在七〇年代以後,開啟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的一系列論爭?
作者介紹
施舜翔
施舜翔 Paris Shih
台灣台北人。畢業於政治大學英國文學研究所。
研究興趣為莎士比亞,珍奧斯汀,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性別與情慾史,流行文化政治。
二〇一五年創立學術網站「流行文化學院」,現為「流行文化學院」總編輯。
著有《惡女力:後女性主義的流行電影解剖學》、《少女革命: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化史》。
個人網站|shihparis.com
目錄
序/在地雷區舞蹈
第一部:文學論戰
──誰怕吳爾芙:女性主義文學經典論戰
──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閣樓上的瘋女人:《簡愛》的女性主義論戰史
第二部:性論戰
──性革命:從金賽性學到女性情慾新浪潮
──性論戰:反色情與性激進的女性主義戰爭
──性別惑亂:從女同志連續體到T/婆美學
第三部:文化論戰
──壞教慾:羅曼史與女性主義愛恨史
──千面女郎:電影與女性主義觀看史
──偷穿高跟鞋:時尚與女性主義爭議史
試閱
誰怕吳爾芙:女性主義文學經典論戰
「女人若要寫作,一定要有錢與自己的房間。」
一九二八年十月,當吳爾芙在劍橋大學的紐納姆(Newnham)與格頓(Girton)學院進行系列演講時,她意圖釐清女人與創作之間的歷史關係。這系列演講的原稿因此名為〈女人與創作〉(“Women and Fiction”)。當然,吳爾芙對女人與創作的反思,絕對無法容納於幾場演講之中。因此,她在隔年將原稿擴充改寫。後來我們知道,這篇文章會成為眾人耳熟能詳的女性主義經典,《自己的房間》。
〈女人與創作〉是《自己的房間》的前身,兩者在文學舞台上卻有著迥異的登場方式。一九二九年三月,當〈女人與創作〉出現於《論壇》(The Forum)雜誌時,《論壇》編輯搭配莎弗(Sappho)、珍奧斯汀與喬治桑(George Sand)的肖像,透過文學史上一系列女作家的並置,將這篇文章打造成高雅的文學評論。同年十一月,在《自己的房間》正式出版一個月之後,吳爾芙卻決定在《時與潮》(Time and Tide)雜誌發表兩篇節錄。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決定。畢竟,《時與潮》雖然以左翼政治著稱,支持女性主義思想,在戰間英國卻佔據了曖昧的文化位階,廣納了通俗的大眾議題。對比《論壇》雜誌對吳爾芙的高雅再現,《自己的房間》在《時與潮》中甚至連同商業廣告一起現身。吳爾芙的意圖很明顯──她要讓這本書走出文化菁英的藩籬,實際接觸女性大眾1。
吳爾芙成功了。《自己的房間》不只走出文化菁英圈,更以超乎想像的規模,成為席捲全球的女性主義經典。這樣的暢銷與流行,或許是吳爾芙當初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還有一件事情,可能同樣超乎吳爾芙的想像之外。《自己的房間》雖然批判了父權社會對女性創作的壓抑,勾勒出女性書寫的理想境界,卻在八〇年代引發了女性主義學界最轟動的一場論戰。在《自己的房間》出版半個世紀以後,吳爾芙不只成為女性主義的全球符號,更成為性別研究的爭議人物。從此,當女性主義者提到吳爾芙,她們想像的不再是浪漫的神話,而是激烈的爭戰。
究竟吳爾芙如何因為《自己的房間》,化身二十世紀最受爭議的女性主義文學象徵?
誰怕勃朗特:《自己的房間》作為文學批評
在進入戰火中心以前,我們或許需要重讀一次《自己的房間》。在這本書中,吳爾芙重探女性寫作的歷史情境,並銳利批判掌有大量資本的男性學術體制。她虛構出一座「牛橋大學」(Oxbridge),讓敘事者「瑪麗畢頓」(Mary Beton)漫遊其中,以諷刺筆調揭露男性掌有的權力與資源,以及對女性進行的排除與隔離2。
不過,比較少人注意到,《自己的房間》本身也是文學評論。某種程度上,這本書甚至可以說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的祖師奶奶3。 吳爾芙爬梳歷史上的女性詩作,從十七世紀女詩人溫契爾西夫人(Lady Winchilsea)與卡文迪許(Margaret Cavendish)的詩句中,發現暗藏的憤怒之火。吳爾芙堅持,早期女性作家壓抑的憤怒扭曲了她們的作品。
從這股憤怒之火,吳爾芙延續到十九世紀的女性小說家。吳爾芙認為,勃朗特和十七世紀女詩人一樣,將太多的憤怒注入《簡愛》之中,而這樣強烈的情緒,使得勃朗特無法完全釋放自己的才華:「當她應該冷靜書寫時,憤怒佔據了她。當她應該理智書寫時,愚昧佔據了她。當她應該書寫角色時,她在寫自己。」吳爾芙不滿《簡愛》的除了難以壓抑的憤怒之外,還有勃朗特顯而易見的個人聲音;《簡愛》原可擁有更清晰的視野,卻受制於勃朗特的顧影自憐4。 對吳爾芙來說,珍奧斯汀是更為理想的書寫典範,因為她能夠迴避女性作家的憤怒,不受負面情感影響,不受男性批評干擾,冷靜而客觀地書寫。吳爾芙在此解釋,一個小說家應該保持寫作的「誠實不倚」。勃朗特因為自己的怒火犧牲了誠實不倚的原則,而珍奧斯汀做到了5。
在《自己的房間》最後,吳爾芙承接自己對女性作家的討論,提出了「雌雄同體」(androgyny)的寫作典範。她主張,一個真正理想的寫作心靈,必須同時擁有「男性」與「女性」。過度意識自己的性別是危險的,單有一個性別也是危險的。一個作家若要創造出理想的作品,便要讓心靈中的「男性」與「女性」攜手合作,永結同心。在吳爾芙眼中,莎士比亞、濟慈(John Keats)、蘭姆(Charles Lamb)與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達到「雌雄同體」的理想。相較之下,彌爾頓(John Milton)、強森(Ben Jonson)、沃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與托爾斯泰(Leo Tolstoy)則過於「男人」。而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雖可稱得上是「雌雄同體」的代表,卻還是偏向「女性」一些。
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中表現出超脫與冷靜,不過,我們不禁想問,她的書寫能夠跳脫負面情緒、擺脫性別意識嗎?《自己的房間》的幽默諷刺中沒有潛抑的怒火嗎?《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的意識流動中沒有隱藏的焦慮嗎?這時,七〇年代末最有名的女性主義學者忍不住質疑,吳爾芙的冷靜不是超脫,吳爾芙的諷刺不是解放,吳爾芙也有勃朗特的焦慮、恐懼與憤怒,而她口中的「雌雄同體」理想,只不過是一種「逃逸」。
那個人的名字叫淑華特(Elaine Showalter)。
──
註:
(1) 關於《時與潮》的文化位階與《自己的房間》的出版脈絡,見 Melissa Sullivan, “The ‘Keystone Public’ and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Time and Tide, and Cultural Hierarchies,” in Virginia Woolf and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 ed. Jeanne Dubino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67-79.
(2) 很多人將《自己的房間》視為吳爾芙的自傳式散文,因此忽視敘事者「瑪麗畢頓」的存在。瑪麗的出處是十六世紀的歌謠〈四個瑪麗之歌〉(“Ballad of the Four Marys”),其中包括瑪麗畢頓、瑪麗賽頓(Mary Seton)、瑪麗卡麥寇(Mary Carmichael)以及瑪麗漢米頓(Mary Hamilton)。值得注意的是,「瑪麗畢頓」不是傳統小說中穩固的敘事主體,敘事聲音疏離、分裂且游移。莫伊將此敘事策略連結到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對單一性別主體位置的解構。見 Toril Moi, Sexual/ 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1-18.
(3) 不少學者視《自己的房間》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奠基之作,也有學者指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原型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紀,甚至是中古時期。關於吳爾芙之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關係,見 Jane Goldman, “The Feminist Criticism of Virginia Woolf,” in A History of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eds. Gill Plain and Susan Sell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6-84.
(4) 不過,後來也有女性主義學者替勃朗特辯護。卡普蘭(Cora Kaplan)便指出,吳爾芙刻意將《簡愛》中的女性怒火簡化為「個人的不滿」。她進一步主張,吳爾芙對《簡愛》的攻擊出於防衛心理,底下潛藏的其實是對勃朗特的認同。見 Cora Kaplan, Victoriana: Histories, Fictions,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
(5) 有趣的是,珍奧斯汀的冷靜,正是勃朗特不滿珍奧斯汀的原因。在寫給路易斯(George Henry Lewes)的信件中,勃朗特形容珍奧斯汀的小說宛如「一座設上藩籬、精心栽培的花園,有著清楚的界線與嬌貴的花朵,但是沒有開闊的鄉野,沒有新鮮的空氣。」她強調,自己絕對不會想住在奧斯汀的小說世界裡。勃朗特對奧斯汀的評論不只是單純的批評,也標示出兩種書寫模式──奧斯汀的寫實筆法對上勃朗特的歌德想像。不過,珍奧斯汀的小說其實也包含歌德元素,兩人的書寫共享了不少特色,不應被視為二元對立的存在。
推薦序文
序/在地雷區舞蹈
一九八〇年,卡拉德尼(Annette Kolodny)在《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上發表〈舞過地雷區〉(“Dancing through the Minefield”)。所謂的「地雷區」,指的是女性主義批評家在學院中面臨的重重危機。男人要不是指控她們扭曲文本,誤讀經典,就是嘲諷女性主義批評前後矛盾,散亂無章。相較於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女性主義批評似乎難以溯及單一源頭,缺乏中心思想。面對這樣的控訴,卡拉德尼倒不急著彰顯女性主義理論的共同根基。相反的,她坦承,女性主義批評的「去中心」正是她驕傲擁抱的特色。對卡拉德尼來說,所有的女性主義閱讀都是平等的。相較於中心思想,女性主義者應當擁抱「愉悅的複數主義」(“playful pluralism”),視多元差異為女性主義的可能,而非侷限。
出乎卡拉德尼意料之外,〈舞過地雷區〉一出版便引發爭議。有人說,女性主義批評不像卡拉德尼描述得那麼缺乏體系,至少可以分為自由、基進與社會主義三條路線;有人不滿卡拉德尼只提及白人異性戀批評家,忽略了黑人與女同志;更有人說,卡拉德尼表面上擁抱「複數主義」,實際上卻打算把「好女性主義者」送入學院,建立權威1。 卡拉德尼原想邀請女性主義夥伴一同拆除地雷,好讓後輩能以輕盈的姿態「舞過地雷區」,最後卻反過來開闢另一片戰場,點燃女性主義學界的熊熊戰火。
當然,學界針對卡拉德尼的批評不盡公平。卡拉德尼自己說了,她在文章開頭提及的女人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女同志;而黑人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貢獻,是她在下一篇文章才要專心處理的主題。之所以不以自由、基進與社會主義來區分女性主義批評,是因為她相信流派的界線曖昧模糊,難以對應文學評論的複雜面向2。 但是,卡拉德尼真正的盲點,或許不在於對流派的迴避,也不在於對黑人與女同志的忽視,而在於她還沒意識到,女性主義閱讀並不總是「平等」的,女性主義者所面對的批評聲浪也並不總是來自男人。一九八〇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示的不只是女性主義理論得來不易的學院認可,更是女性主義運動無從掩飾的內部矛盾。是這樣的內部矛盾粉碎卡拉德尼的烏托邦理想,讓我們明白,談女性主義,我們不可能只談多元,不談衝突;只談流派,不談分裂。一旦迴避衝突與分裂,女性主義的歷史就不可能完整。
《性、高跟鞋與吳爾芙》正是一部由衝突與矛盾組成的女性主義史。書名的靈感來自六〇年代的經典神話:性、藥與搖滾樂。這三個元素分別象徵了女性主義論述的三大戰場。吳爾芙(Virginia Woolf)對應的是女性主義者的「文學論戰」。對很多人來說,珍奧斯汀(Jane Austen)、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與吳爾芙是無庸置疑的「女性主義作家」,《簡愛》(Jane Eyre)與《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也是無庸置疑的「女性主義經典」;對八〇年代的女性主義學者來說,這些「經典」卻是開啟論戰的起點。我們將看到《自己的房間》如何在八〇年代掀起文學界的世紀論戰,體現出英美與法國女性主義在大西洋兩岸的激烈衝撞;珍奧斯汀如何點燃女性主義者的「思想之戰」,間接推動酷兒文學批評的發展;《簡愛》又如何引發女性主義學界的「內在革命」,化為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核心戰場。這些論戰一再告訴我們,沒有永恆的「女性主義經典」,也沒有不變的「女性主義閱讀」,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在半個世紀以來,反覆開啟女性主義學界的詮釋戰爭,讓我們得以透過文本的裂縫,一窺情慾、階級與殖民問題的多重矛盾。
性對應的當然是「性論戰」(feminist sex wars)。作為核心爭議,性論戰幾乎貫穿了整部女性主義當代史。一般而言,我們將一九八二年的「巴納德性會議」(the Barnard Sex Conference)視為女性主義性論戰的起點。不過,性論戰有前因,也有後果。我們將回到二次大戰後的美國社會,看看戰後性學如何帶起女人的「性革命」,而女性主義者對「性革命」的矛盾情結,又如何間接導致八〇年代的「性論戰」。我們也將重返巴納德性會議,以及「巴納德」前後的相關戰爭,看看「反色情」(anti-pornography)與「性激進」(sex radical)的意識形態矛盾,如何從七〇年代下半葉的舊金山灣區一路延續至今。當然,性論戰不只是女性主義的,更是女同志的。從七〇年代起,「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與「性激進女同志」對性政治的詮釋歧異,掀起了女同志社群內部的激烈論爭。一如文學論戰,「性論戰」體現了性別、情慾與種族的複雜交織,迫使我們看見黑人、T/婆與愉虐實踐者的地下慾望。這是為什麼,女性主義的性論戰會間接催生「酷兒理論」(queer theory),讓酷兒學者在九〇年代以後,繼承性論戰的思想遺產,開闢屬於自己的全新戰場。
最後,高跟鞋象徵的是女性主義者的「文化論戰」。如果有什麼與色情同等爭議的話題,那顯然是同樣出自文化工業的時尚、羅曼史與好萊塢電影。在早年女性主義論述中,「反時尚」與「反羅曼史」是普遍的立場;自七〇年代下半葉起,新興的女性主義學者接連翻轉通俗文化的既有定義。羅曼史原先被視為洗腦女性大眾的「讀/毒物」,卻在精神分析與讀者反應理論的重新詮釋之下,化為抵抗婚姻與家庭體制的「雙重文本」;時尚原先也被視為箝制女性身體的工具,卻在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嶄新視野之中,化為改寫性別與慾望結構的重要媒介。如果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好萊塢電影單單滿足「男性觀者」(the male spectator),八〇年代以降的女性主義者則強調女人進行「跨性認同」(trans-sex identification)、「同性凝視」(homoerotic gaze)與「酷兒閱讀」(queer reading)的可能。這一系列的辯證不只讓陰性文化產物獲得學界重視,更讓流行文化發展為另一個核心的女性主義論述戰場。
無論是性論戰、文學論戰還是文化論戰,一波又一波的爭議提醒我們,女性主義未必照著「流派」平行發展,也未必循著線性敘事前進。曾有人說,女性主義終有一天會死去,因為我們將會抵達性別平等的未來。但這樣的說法預設的是女性主義的進步史觀,性別政治的齊頭並行。在寫完這本書的當下,我反而深信,女性主義不會有死去的一天。只要還有矛盾的可能,曖昧的空間,女性主義就會反覆重生,不斷進化,持續伴隨我們在地雷區上無畏地舞蹈。
──
註:
(1)關於女性主義學界對〈舞過地雷區〉一文的批判,見 Jane Marcus, “Storming the Toolshed,” Signs 7.3 (1982): 622-40; Judith Kegan Gardiner, Elly Bulkin, Rena Grasso Patterson, and Annette Kolodny, “An Interchange on Feminist Criticism: On ‘Dancing through the Minefield,’” Feminist Studies 8.3 (1982): 629-75.
(2)關於卡拉德尼對自己的辯護,見 Kolodny, “An Interchange on Feminist Criticism,” 665-75.
NT$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