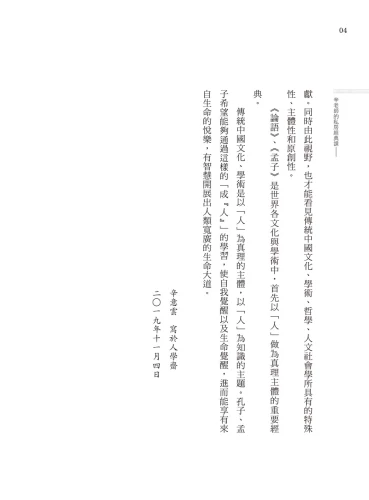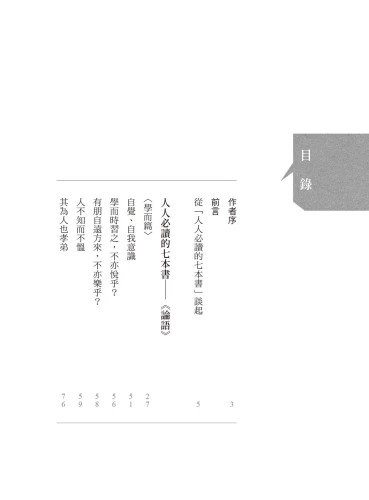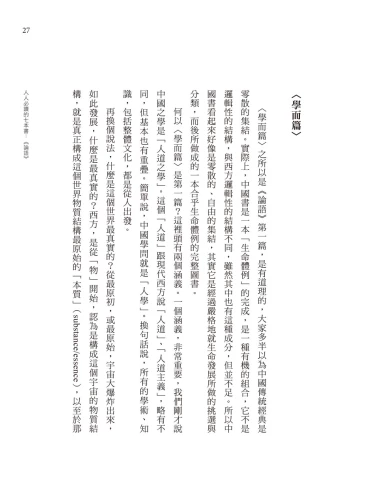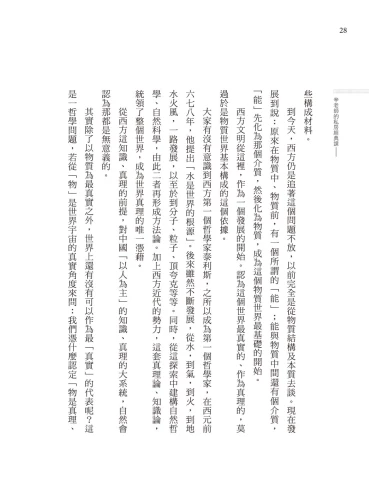人人必讀的七本書:《論語》、《孟子》辛老師的私房經典課(1)
商品編號:00050021
定價: 400 元
優惠價: 79折 316 元
優惠活動
購買提醒
本商品為出版已久的書,出版已久的書容易產生些許的黃斑、或有些許瑕疵(例如:壓痕、褪色等),不影響內文閱讀。每本書況不盡相同,請考慮評估後再購買結帳,採取隨機出貨。
如想進一步了解書況詳情,可以來信 cptw1897@gmail.com ,或點擊右上角「 客服 」留言詢問,感謝您支持臺灣商務印書館。
內容簡介
論語──給我們安心、安身、立命。
孟子──給我們性善民本的處世哲思。
孔孟之道以「人與人性」為主體,
自我覺醒以及生命覺醒,
進而享有來自生命的悅樂,開展智慧。
儒家思想是一種代代更新的思想,
為現實人生尋求最適當、最廣闊的生命位置。
我們要如何了解傳統經典,從中汲取智慧?
閱讀這門技藝,讓我們可以穿越時空,思索解讀。
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不只可落實於現代或當下,
亦可見其在時間脈絡中不朽的刻痕。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提出人生中七本重要必讀之書,因傳統思想從中貫穿,可以認識中國文化與學術,極為重要,但一般大眾又該怎麼讀?
辛老師的私房經典課,由熱愛閱讀的辛意雲老師親自為讀者大眾解惑,特以三冊,獻給讀者作為人生必讀的案頭書。
作者承接錢穆先生提出人人必讀的七本書,包含:《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將這七本經典深入剖析,供讀者作為人生的閱讀參照。作者曾受邀講述此系列課程,深入剖析,如今因應廣大讀者的期盼親自重新編寫增訂,十分精闢而珍貴,期望能為讀者解惑之外,更可讓大眾理解傳統文化的奧祕,並落實於現代生活。
此系列共約五十萬字,預計分為三冊出版,第一冊為《論語》、《孟子》,第二冊為《莊子》、《老子》,第三冊為《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讀者可依序閱讀,貫串七書之思維邏輯。傳統經典以新眼光新視界展讀與理解,更可見其雋永及現代性。
「人人必讀的七本書」共三冊:
《人人必讀的七本書:論語、孟子》——辛老師的私房經典課(1)
2020年新書預告
《人人必讀的七本書:莊子、老子》——辛老師的私房經典課(2)
《人人必讀的七本書: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辛老師的私房經典課(3)
第一冊:《論語》、《孟子》建立了「人學」。
第二冊:《莊子》、《老子》看見生命自由的真諦。
第三冊:《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了解宇宙與生命的內在秩序。
儒家最大的特質,就是代代依著新的思想,提出新的生命價值、新的生命哲理。所以儒家代代更新,從漢以後幾乎沒有「純粹不變」過。而中國的各家,其實最後也都回歸到儒家的本身,因為不離開:為現實人生尋求最適當、最廣闊的生命位置。
錢先生那時候給我們上課,他說:「你們是二十世紀的人,科學發展到今天,今天的儒家,你們說,該以何為立?你們將嘗試認識現代科學,認識現代代表性的新知識,然後如何融會貫通,為現代人尋找:在今天這樣一個大科學、大宇宙論、大經濟社會如此發展的時代裡,人安心、安身、立命之處。這樣才是儒家,才是『大儒』也。儒家代代更新,無須標立『新儒家』,所以我沒有參加張先生(張君勱)的邀約,我婉拒了『新儒家』的簽署。」
然後他再說:「今天讀書人關心傳統中國學術,基本上應讀七本書。那七本書你們看起來好像不是儒家,但實際上是今天必讀的七本書。因為中國思想從中貫串,你讀了,就知道什麼是中國文化,什麼是中國學術。」
我們今天起就開始談這七本書。這七本書就是《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
——選摘1
我們今天所談的問題的因緣,從這裡開始:一個是知識的前提;一個是錢先生所提出,什麼是真正的儒家?而真正的儒家,要能夠有一個心量—這個心量關懷人生、尊重生命,肯定人;同時還有一個寬廣的心胸,與「自我意識」在開發出來後的高度智慧;有能力認識新世界的發展、新知識的發展,而將它消融,至少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最健康的大道—古典的說法,「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我們的課從這裡談起。
——選摘2
作者介紹
辛意雲
辛意雲
師承錢穆先生,現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長期宣講儒學及其精神、中華文化,希望能讓大眾的日常生活,享有傳統國學之美,體驗古人所展現的生命情調。曾參與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製作。2008年接受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新竹IC之音廣播電台的共同邀請,開設《論語辛說》節目,以深入淺說的方式詮釋孔子語錄,頗受各界好評。2010年獲得第十四屆台北文化獎,爾後陸續推出《論語辛說》、《莊子辛說》、《墨子辛說》、《老子辛說》系列有聲作品。
長期在台北藝術大學授課,也長年指導建國中學國學社達四十餘載,講說國學經典,致力開啟學生的心智與潛能,讓學生在生活節奏快速的現代,仍能體會傳統文化的底蘊,開展智慧。著有《辛老師的私房國文課:從經典中學習生活智慧》、《辛老師的私房美學課》等。
目錄
試閱
選摘一
「人人必讀的七本書」這個活動是源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合辦的講座,主要因素之一是四書很可能又會回到我們的中學教育之中。因此文化局、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和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提供這麼一個場地,來向大家報告傳統中國的經典,它的大義是什麼,還有怎麼去讀。
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人都認識基本中國字,所以任何中文書,拿起來,我們都可以讀。再加上,中國的經典多半牽涉我們現實人生裡的活動與事情,所以大家也就容易從現實人生中來看待它。而中國經典的特殊處,就在從現實的經驗中看待,能夠對人有很大的幫助,也解得通,所以如此一來,大家就覺得傳統經典遺留下來的學術性重要著作都貼近現實人生。
但是實際上,人們忽略掉的是,我們的現實人生是極其複雜的。
就像日前發的新聞,一則暴力鬥毆事件。女子因口角與男友一起毆打計程車司機,那麼嬌美的一個年輕女孩,卻有判若兩人的表現。那位男友一表人才,可是暴怒起來,每一拳都似乎可以致人於死,但等到他面對社會大眾,卻可以跪地磕頭。這種極端性,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對立,這是人格分裂嗎?
我們今天能在這個活動中,看到這個事件,不知道會不會引動大家看到,所謂的現實人生,其實是極其複雜。就如零與一之間,除了這兩個極端,我們看到這中間可以做無限分割的小數點。
不僅如此,今天在座者有不同的年齡層,你們想想,如果你是四十歲,你跟三十歲時的你,是否有差距?如果你是三十歲,你跟二十歲時的你有沒有不同?如果你是六十歲,你跟三十歲時有沒有不同?我們回溯到兩歲半,那個你,就是現在的你嗎?好像截然不同的兩個個體,然而卻又是同一個你。
所以即使是現實的生命經驗、生活的活動,它的複雜性乃是出乎人意想的。
這相對於太空,太空倒反而簡單、單純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如此?可是我們總覺得「科學」是複雜的,其實不然。而傳統中國經典所記錄的乃是這些複雜的人的事。
但是今天人們在讀這些傳統經典,大家很容易輕忽了其中的深度與廣度,看到坊間所講的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這些經典,似乎都只限於通俗的日常人生,或提供一點世俗的道德規範,而更多是一些人際交往的伎倆或聰明,以求用較高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傳統經典就變成了非常「實用」,充滿了伎倆和手段的一些經驗紀錄。如此,相對於西方的知識及知識經典,傳統中國經典似乎欠缺提升人性的重要成分,只是通俗實用小品了。
然而,中國傳統經典、中國學術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每當朋友要我談有關中國學術的時候,我總忍不住要舉一個例子,因為這是流行於海峽兩岸,說不定所有華人的地區,或所有探討華人學術的地區,都可能這樣認為。這也是我所教的學生,當他們進了大學,他們提出問題說:學校裡老師告訴他們,中國沒有學術可言;因為中國沒有一個概念是可以被明確定義化的。就以中國的學術說「仁」作為最重要的知識前提,只是「仁」字,單單在《論語》裡面,就有一百零九處不同的說法;重要的解釋大概是七十九個,再濃縮,也有四十九個。那你說,到底「仁」是哪個?不能確定,無可定義,這如何作為知識的前提?所以中國的學術只是一些經驗的集結。我們今天建立中國學術,只做文獻研究、資料的整理,不做任何知識意義的探索,因為無可探索,因為每一個詞有其歧義性,也就是不同的意義太多了。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西方的大學問家,最有名的黑格爾已經這麼說了。不僅黑格爾,甚至英國的一個大思想家,他也在他著名的著作裡講:中國基本上沒有學術,因為中國沒有進入到科學的世界裡,中國仍然是在「前科學時代」,只有經驗的集結,沒有任何理論的建構,原因是,中國的字義無法統一,是多重的,是歧義的。雖然中國發展出這麼多的文明的事物,然而在知識上是缺空的。
現在凡是以西方的知識方法作為前提的,幾乎也都是從這個觀念裡來談。在不知不覺間,第一,否定了中國。換言之,中國五千年下來、兩千五百年下來,在學術上其實是空的,而這是個事實嗎?我們身為現在21世紀的人,還值不值得來學這些東西呢?
第二,不知不覺中,人們或世界各地的學者,在知識,在真理上,就都以西方的知識、西方的真理,當作唯一的真理以及知識了。(略)
這第二個因緣,就是起於錢先生。
近來在我們華人學術圈裡,也有一個公案。因為現在大陸也開始談原有的傳統中國文化、學術了,學者似乎劃定一條界線:凡在海外,或者1949年之後離開大陸,談中國學術,或者還強調儒家的重要性者,他們就稱之為「新儒家」。
不過「新儒家」這個名詞,基本上其實有兩種涵義。我正好藉這個機會,也就提出。因為我們今天要談的這七本書,其實是因緣於關鍵的一條線,是從「新儒家」的問題談起。
如果是以民國三十八年離開大陸,同時仍以傳統中國文化與學術為主,談儒家——孔孟之道,就全稱他們為「新儒家」,這是一條線;如果認為舊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新時代中,需要積極為儒家、為中國傳統學術尋找一條新出路,想將儒家思想與這個時代接軌的人,他們依西方學說,說儒家也有如西方的方法論、知識論、形而上學、宇宙論、本體論……這些學者做這些努力,這又是一種新儒家,大陸學界把他們稱為「新儒家」,這是另一條線。不過他們把錢穆賓四先生歸入後者「新儒家」。
因此記者訪問錢先生:「您是新儒家嗎?」因為當時張君勱先生邀請了四位學者——錢穆先生、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向世界發表了《新儒家宣言》,來向世界說明儒家的重要性,標榜「新儒家」。只是錢先生婉拒了。現在有人說那是因錢先生跟他們有不同派別。其實這說法似是而非。
重要的是,錢先生說:「自古所謂的儒家,是代代更新的,無所謂新儒家。」
今天的時代,從新文化運動,甚至從清代中晚期,一些儒者反對長期以朱子對四書的注解,作為考試的唯一標準答案,認為凡宋明理學所說的,都是錯的,然後建立起清代的學術派別。
當然,宋理學成為元末、明清科舉考試的唯一真理標準,限制人們、學者的思考,因此清學者有人站出來,反宋理學、朱子之學,並形成「漢學」,考據之學。
於是漢、宋學壁壘分明。清代中期後,儒者提出了漢代對經典的解釋,漢學、宋學對立。他們批判宋代夾雜太多佛教禪宗思想,所以宋理學不是純儒家了,它是佛家的另一種表現。他們說,宋明理學全是教人打坐,怎麼可能是純粹的儒家?純粹的儒家有打坐嗎?孔子會打坐嗎?
可是宋學學者也堅持說,漢朝董仲舒也非純儒啊!夾雜了法家、陰陽家思想,他怎麼可能是純儒?
而後再加上新文化運動的主張者,接受西方的學術標準,一切要求純粹。於是大家探討:到底什麼是儒家?要求「純粹的儒家」。回頭一看,好像都不純粹。而後政治的關係,張君勱提出「新儒家」。
其實,錢先生講,自孔子建立儒家,賦予「儒」新的意義:孔子從「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說起,並講「君子不器」,並勉勵子夏「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而君子儒的特色就是「通達一切」。這也就是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論語之所以為論語,在於他如何以「覺」、以「仁」作為人性的基礎,再通向整個人生,上通向於天,下達普遍於社會,開展出幸福人生。
而後,經過戰國,孟子對墨子、楊朱雖有所批判,但孟子在批判中,清楚表現出他接受了墨子的思想,也接受了楊朱的思想,並綜合提出所謂的仁、義,作為儒家的標榜。我們看論語中「義」字並沒有「仁禮」重要,論語中「仁、禮」並稱。「義」在論語中只提了四次。但由孟子接受墨子「義」字的觀念,「義」在儒家擴大了重要性,仁、義、禮、智,加上信,成為儒的五行、五德。
到了漢代,陰陽家的宇宙觀、老子的思想、莊子的觀點、法家的原則,又化為儒家思想的部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是一個綜合性的思想,它帶著強大、原本孔子未曾碰觸的宇宙論,提供了漢代人如何在這樣一個巨大新社會中,找到適當的位置。
魏晉南北朝何嘗不是如此?「玄學」的提出,在宇宙本體的探討後,再確定人生的位置,而後大乘佛教的發展,更將當時中國人所面對的世界,無限制地開闊起來。
特別是隋唐,提出了「空」的觀點,是那個時代最精采的思想。
宋明理學,重新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最後歸本於儒,確定宇宙中生命的秩序,在這個新宇宙觀裡,再尋找人將如何安頓,同時有著無限開闊的未來。
如此一路下來,儒家最大的特質,就是代代依著新的思想,提出新的生命價值、新的生命哲理。所以儒家代代更新,從漢以後幾乎沒有「純粹不變」過。而中國的各家,其實最後也都回歸到儒家的本身,因為不離開:為現實人生尋求最適當、最廣闊的生命位置。
錢先生那時候給我們上課,他說:「你們是二十世紀的人,科學發展到今天,今天的儒家,你們說,該以何為立?你們將嘗試認識現代科學,認識現代代表性的新知識,然後如何融會貫通,為現代人尋找:在今天這樣一個大科學、大宇宙論、大經濟社會如此發展的時代裡,人安心、安身、立命之處。這樣才是儒家,才是『大儒』也。儒家代代更新,無須標立『新儒家』,所以我沒有參加張先生(張君勱)的邀約,我婉拒了『新儒家』的簽署。」
然後他再說:「今天讀書人關心傳統中國學術,基本上應讀七本書。那七本書你們看起來好像不是儒家,但實際上是今天必讀的七本書。因為中國思想從中貫串,你讀了,就知道什麼是中國文化,什麼是中國學術。」
我們今天起就開始談這七本書。這七本書就是《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
推薦序文
作者序
寫在《論語》、《孟子》出版之前
在進入「工業4.0」的時代,華人能不能站在世界文化、學術、哲學、人文社會學的知識高度上,盱衡人類世界,而理解人類文明的成就與貢獻?同時,能不能也從這個高度,回看傳統中國文化、學術、哲學、人文社會學等,在這世界文明中居於甚麼位置?以及對人類世界文明的貢獻?
換言之,在這新時代之際,華人需要一個寬廣的視角,把中國傳統的文化、學術、哲學、人文社會學等知識,放到世界的大歷史中去看。從這個視點去看,或許才真正地看見自己先人所做的努力與創造。
這也才能讓世界知道,這大歷史中:文化中的中國、學術中的中國、哲學中的中國、人文社會學中的中國,在人類世界的大歷史中的特殊位置以及為人類文明所做的貢獻。
同時由此視野,也才能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學術、哲學、人文社會學所具有的特殊性、主體性和原創性。
《論語》、《孟子》是世界各文化與學術中,首先以「人」做為真理主體的重要經典。
傳統中國文化、學術是以「人」為真理的主體,以「人」為知識的主題。孔子、孟子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成『人』」的學習,使自我覺醒以及生命覺醒,進而能享有來自生命的悅樂,有智慧開展出人類寬廣的生命大道。
辛意雲 寫於人學齋 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NT$316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