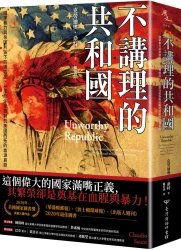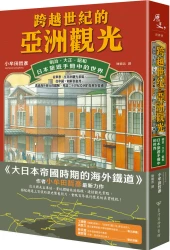咖啡帝國:勞動、剝削與資本主義,一部全球貿易下的咖啡上癮史
商品編號:07010024
定價: 620 元
優惠價: 66折 409 元
優惠活動
內容簡介
第一本爬梳咖啡種植與全球貿易關係的經典著作
「一部令人大開眼界的歷史」、「社會政治分析精細」、「資料豐富的原創性研究」
《波士頓環球報》、《經濟學家》、《衛報》、《出版人週刊》等全球媒體齊聲讚譽
從十六世紀歐洲首次記載咖啡為始,不過四百年,咖啡席捲了歐陸與美洲,成為人們的日常飲品。資本家的銳利眼光,讓他們走入未開發的中南美洲,用利潤與當地政府交易,打著「自由主義」的大旗,一舉改變中南美洲的地景。當咖啡豆在中南美洲種下,帝國主義與奴隸制度隨即而來,資本家用「饑餓」綁架了龐大數量的印第安人,用「工廠制度」包裝讓人嗤之以鼻的奴隸制度,而最後,用令人驚豔的包裝與言語,遮蓋了咖啡背後的血腥。
在拉丁美洲「咖啡國王」詹姆斯.希爾,建立了當地最密集、最盛行的咖啡帝國。咖啡豆從咖啡莊園中出產,隨即送到美國,經過舊金山的烘焙工廠、再到各個城市的超商、廚房,成為消費者手中的罐裝飲料。咖啡成為連結全世界的重要商品,它打破了人體運作與國際政治的既定思維,扭轉了全球貿易的既定形式:當咖啡不再只是飲品時,對於咖啡飲用者而言又代表了什麼?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始,全球貿易天翻地覆的改變,新的連接卻意味著更深一層的分歧,到一九五○年時,工業化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未開發國家的五倍!當世界貧富的劃分與咖啡飲用者和咖啡工人的劃分一致、當咖啡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重要的商品,咖啡不僅「連接了世界」,更在大西洋劃出了貧窮與富有、獨裁與自由的巨大鴻溝。當咖啡串起了世界、隔閡了窮人跟富人,讓人不禁想問:
▶當資本家與生產主義結合,咖啡處理廠中的工人與機器有無差別?
▶當咖啡莊園等同於饑餓,國家該保護的是工人還是咖啡?
追溯百年來咖啡種植的發展,呈現一齣全面的「咖啡上癮史」
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奧古斯丁.塞奇威克從消費與生產的角度,講述了咖啡與資本主義之間盤根錯節的故事。一覽咖啡如何登上歷史舞台、如何被創造與革新、如何導致種植園的饑餓、如何引爆一波又一波的紅色起義,以及最終,影響我們如何看待手中的咖啡。
作者介紹
奧古斯丁.塞奇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
奧古斯丁‧塞奇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
哈佛大學博士,在紐約城市大學任教。他對全球飲食,工作和資本主義歷史的研究獲得了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和哈佛大學的正義、福利與經濟學項目的研究金,並已發表在History of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Labor。他最初來自緬因州,居住在紐約。
譯者簡介
盧相如
盧相如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目前為自由譯者,喜歡閱讀小說。譯作有《最後的外科醫生》、《記憶游離》、《凌空之夢:1974,我在世貿雙塔上走鋼索》、《告訴你有多好吃:我的第一本美食寫作書》、《滾貓不生苔:貓咪教你的人生哲學》、《大草原的奇蹟》等。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專文推薦
奧地利維也納獨立咖啡學院最高階咖啡師 鄭華娟
聯合推薦(依筆畫順序排列)
生態綠董事長 余宛如
臺灣咖啡研究室計畫主持人 林哲豪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宋世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褚縈瑩
《咖啡帝國》將改變我們往後人生中所喝的每口咖啡。薩國不只單指薩國,咖啡也不單是咖啡本身,而是現代社會美好與矛盾方方面面的縮影,有如混合了民主政治、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綜合配方。其驚心動魄與令人流連的餘韻,不亞於我桌上剛喝完的那杯精品咖啡。咀嚼其中,才知道其中美味與隱藏在其後苦澀的由來。
──臺灣咖啡研究室計畫主持人 林哲豪
《咖啡帝國》作者奧古斯丁.塞奇威克真的是說故事的大師,從薩爾瓦多資本家詹姆斯.希爾的角度出發,寫了一個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精彩咖啡故事。這讓手中的咖啡不只是咖啡,而是一個傳奇的延伸,也是看穿資本主義與當代消費社會之間密不可分關係的關鍵切入點。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宋世祥
《咖啡帝國》文筆極為優美,絕不僅僅是堆疊剪裁史料;儘管文字常帶情感,卻未流於浮泛的批判。我相信《咖啡帝國》已經為全球史與商品史的書寫開拓了新的視界。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這本書中文版的問世,將更開闊我們的全球視野,同時縮短了咖啡愛好者與專業咖啡歷史的距離;這是一本喜愛咖啡的人,儘量不要錯過的咖啡專業好書。
──奧地利維也納獨立咖啡學院最高階咖啡師 鄭華娟
作者巧妙地以十九世紀的「能量概念」及「熱力學原理」為軸,為讀者開展大英帝國商人在薩爾瓦多咖啡園的勞動力管理策略、鋪陳美國金元外交政策背後的新古典經濟學預設、標示薩國左派游擊隊所本的馬克思剩餘價值論。將一部成功結合科學史、勞工史、商品鍊研究的專業歷史著作,融在流暢的故事裡。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褚縈瑩
◆ 媒體讚譽 ◆
「涉及層面極廣,研究透徹……在抗議文學的傳統中,它更多植根於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而非馬克思。」
——亞當.戈普尼克(Adam Gopnik),《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塞奇威克這部扣人心弦的作品揭露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商品製造的黑暗核心,這項商品每天早晨被人視為珍寶,在工作場所被奉為圭臬,在茶餘飯後受到讚揚。它為以下問題提供了一個具有壓倒性力量的答案:『透過這項日常商品與遙遠國度的人和地方所串起的連結意味著什麼?』」
——柯林.格林伍德(Colin Greenwood),《旁觀者》(The Spectator)(英國)
「難以言喻、令人振奮……《咖啡帝國》是一部資料豐富的原創性研究,它以令人信服的細節顯示了咖啡資本主義在過去兩百年裡,如何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的人帶來了利潤和痛苦、安慰和恐懼……塞奇威克的偉大成就在於替宏觀經濟學披上了溫暖的、會呼吸的肉身。」
——凱薩琳.休斯(Kathryn Hughes),《衛報》(The Guardian)
「精心研究,場景設置生動,社會政治分析精細……《咖啡帝國》將你正在喝的這杯咖啡背後的歷史與現實暴露無遺。」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令人印象深刻……對薩爾瓦多的勞工關係和整個資本主義的有力控訴。」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英國)
「塞奇威克先生的書巧妙地將所有這些線索結合在一起,並將眾多角色交織在一起,它是一個講述關於商品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生產者、消費者、市場和政治聯繫起來的寓言。就像它所描述的飲品一樣,它令人大開眼界以及振奮。」
——《經濟學家》(Economist)
「塞奇威克以其對細節的敏銳把握,透過平凡的咖啡豆故事,描繪了大眾消費市場和現代零售戰略的崛起……《咖啡帝國》所傳達的深刻訊息更加廣泛……咖啡這個當今『無與倫比的提神飲料』,同時也是一個全球化的故事。」
——奧利弗.巴爾奇(Oliver Balch),《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咖啡帝國》(Coffeeland)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它將咖啡的歷史綜覽、人們對咖啡的依賴,以及全球經濟的研究等內容相結合。[……] 塞奇威克不僅考察了咖啡及其來源,而且透過各種學科的方法考察了它對現代社會的全球影響:世界是如何被咖啡所推動,並完全依賴其在世界的經濟穩定。」
——《光譜文化》(Spectrum Culture)
「歷史學家塞奇威克以引人入勝的細節,探討了咖啡作為一種植物、一種作物、一種商品和一種強大的化學物質。」——《書單》(Booklist)
「發人深省,文筆優美……塞奇威克以具有廣度的分析咖啡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令人驚訝,他將歷史人物帶入生活的能力也令人驚訝……[一部]令人大開眼界的歷史。」
——《出版人週刊,星級評論》(Publishers Weekly, Starred Review)
「迷人交織的敘述,使我們每天所飲用的咖啡更加深不見底。」
——《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這個世界不是靠金錢、愛情或性來運轉。它靠的是咖啡。」
——佩德羅.馬塔.桑托斯(Pedro Marta Santos),《薩巴多》(Sábado)(葡萄牙)
「咖啡的確代表了我們的文明——而很多人為此付出了代價。」
——布萊特.埃文斯(Brett Evans),《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澳大利亞)
目錄
導讀 盤根錯節的咖啡資本主義史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推薦序 我們與咖啡的距離 /奧地利維也納獨立咖啡學院最高階咖啡師 鄭華娟
前 言 百年咖啡
第一章 伊斯蘭教的完美象徵
第二章 棉都
第三章 持續併發的火山
第四章 鰻魚
第五章 希爾斯兄弟
第六章 阿波羅的象徵
第七章 不可抗力
第八章 咖啡處理廠
第九章 壞運氣
第十章 饕客
第十一章 傳承
第十二章 咖啡樹洞
第十三章 玻璃籠子
第十四章 饑餓的種植園
第十五章 愛在咖啡種植園
第十六章 關於咖啡的事實
第十七章 美國處方
第十八章 咖啡問題
第十九章 革命種子
第二十章 紅色起義
第二十一章 戰爭引爆
第二十二章 屠殺
第二十三章 堆得高,賣得便宜
第二十四章 杯子背後
第二十五章 戰爭
第二十六章 浴火重生
試閱
前言 百年咖啡
多年以後,海梅.希爾(Jaime Hill,後稱小海梅)回想起自己遭到綁架那天下午,仍不免要怪罪自己的父親。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傍晚左右,小海梅正端坐在書桌前,打算寫信給他的女兒亞歷珊卓。當時萬聖節在薩爾瓦多算是一個嶄新的節日,卡斯楚於一九五九年在古巴發動革命之後,許多家庭遷入該國。「不給糖就搗蛋」的活動,很快就在首都聖薩爾瓦多的高級社區迅速流行起來,時年四十二歲的商人在家族企業中擔任執行者要角,並與家人同住。每一年愈來愈多穿著扮裝服飾的孩子,挨家挨戶進行要糖果的活動,然而為了安全起見,他們通常會搭車前來。即便如此,與即將到來的亡靈節相比,萬聖節的重要性仍因此相形見絀。在十一月初舉行的亡靈節,標誌著豐收季節的開始。
小海梅總是期待著收成季節到來,六個月的傾盆大雨終於換來藍天和微風吹拂,他的興奮之情足以說明這個國家的歷史。由於薩爾瓦多並未靠近大西洋海岸線,因此薩爾瓦多在一八二一年脫離西班牙獨立後便成為「死水」(backwater)。在這片農人自給自足的土地上,該國二十五萬公民中,只有四名律師和四位醫生,每年只有兩到三艘船停靠它的主要港口。這並不是說薩爾瓦多的公民很窮,確切地說,﹁窮﹂是一個相對的字眼,這個國家在商業上孤立的另一面,則是經濟上的平等。十九世紀中葉,在薩爾瓦多下船的歐洲旅客被這裡「沒有極端貧困」,以及土地富饒的景象所震撼。染料和香膏、高收益出口品,在鄉間生長茂盛,甚至連城鎮「都被熱帶果樹所包圍」,其中包括棕櫚樹,橘子,以及「闊葉大蕉幾乎長成一串串沉甸甸的金色果實。」正當外國遊客驚訝於這裡豐饒的自然物產,並看到這裡「非常適合熱帶農作物」生產時,多數薩爾瓦多人皆以集體耕種的土地維生。他們缺乏動力為遠端市場生產新的和不熟悉的經濟作物,更沒有動力為有經濟作物的人工作。按照傳統,該地區自給自足的農民害怕旱季的到來。每年十一月,面對數月的乾旱,薩爾瓦多人像他們的鄰居一樣,祈禱他們賴以維生的雨水回來。
十九世紀末,薩爾瓦多鄉村許多人的生活與數百年前沒什麼區別。太陽升起時,人們沿著狹窄的泥土路、載著農具,這條路從小村莊延伸到遙遠的菜園。傍晚,他們帶著當地市場上可以現吃或是販賣的食物返家。父母教給孩子們以這種方式生活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知識。每年,當氣候出現轉變時,薩爾瓦多人就像他們在中美洲的鄰居一樣,會舉行家族對土地表示感謝的紀念儀式,並藉由裝飾墳墓、跳舞、唱歌、飲酒,呼喚庇佑他們的神靈。然而,其中有些薩爾瓦多人認為這種與過去深刻的延續性並不值得慶祝,他們的眼光望向更廣闊的世界,內燃機、電話和電燈,他們擔心的是自己的國家正在落後,而這群人掌握著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起初改變並不明顯,但在一八七九年之後,薩爾瓦多人賴以維生的農業基礎遭到連根拔起,為開創另一個未來重新墾地。
一八八九年,當小海梅的祖父|當時年僅十八歲的詹姆斯.希爾,從英國曼徹斯特來到薩爾瓦多時,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薩爾瓦多在歷經了兩個世代之後,成了一個全然不同的地方。「最令遊客感到吃驚的改變是」,一位美國旅客在一九二八年寫道,「全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咖啡。一切與咖啡脫不了關係,每個人都直接或間接從事與咖啡相關的行業。」薩
爾瓦多農業部長自身也是咖啡種植者,在同一年說,「薩爾瓦多應該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卻只
關切在單一主題『咖啡』上面。」
儘管在詹姆斯.希爾定居薩爾瓦多的十年間,該地進入咖啡的繁盛時期,不過身為移民,他被禁止擔任政治職務,但在將他的第二母國轉變為現代史上最集中的單一文化國家方面,他可以說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二十世紀下半葉,詹姆斯在種植園和咖啡處理廠中採用的做法,使得咖啡覆蓋了薩爾瓦多四分之一的耕地,種植園雇用了五分之一的薩爾瓦多人口。薩爾瓦多的咖啡種植園,每英畝的產量比巴西高出百分之五十,每年的咖啡產量占該國GDP的四分之一,占該國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因為詹姆斯的幫助,這些出口品最終大部分都被裝在美國超市貨架上顏色鮮豔的罐頭裡,而在同一時期,美國已經遠遠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飲用國家。
一個世紀以來,薩爾瓦多的收成有了嶄新的涵義,專為美國的咖啡飲用市場從事咖啡採摘和加工處理,而咖啡貿易的龐大收入也已不再屬於薩爾瓦多。
在希爾家族,咖啡收成的開始通常意味著唾手可得的回報,但一九七九年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年分。和往常一樣,天氣及時變化帶來了晴朗的天空和乾燥的空氣,非常適合採摘和處理咖啡。然而,這些有利的條件,由於家庭內部和整個國家的發展而蒙上了陰影。小海梅是三兄弟中最年長的,最近其在家族企業中被降職,自二戰以來,他們的家族企業從咖啡發展到房地產、建築、金融和保險。更令人不安的是,昔日的政治衝突死灰復燃,使人們嚴重懷疑該年的收成是否豐盛。百年以來,咖啡將薩爾瓦多一分為二。在這個國家取得非凡的經濟生產力的同時,國家的基礎卻逐漸貧窮。全國百分之八十的兒童營養不良,曾經不存在的「極度貧窮」成了薩爾瓦多的兩個反差之一,另一個則是非凡的財富傳奇「十四大家族」,包括希爾家族在內,最初以咖啡事業起家,在持續經營之下,幾乎壟斷了土地、資源、經濟與政治。這群寡頭政治勢力在國外受過教育,坐在歐洲裝甲汽車的後座上,他們在商業和政府的權勢,使他們受到軍隊、私人保鏢、房屋周圍的高牆,以及其他所有人所保護。薩爾瓦多貧富差距的過程並非沒有受到挑戰,但在歷史上,反對咖啡資本主義的運動卻遭到了可怕的鎮壓,民眾的抗議情緒也一度被轉往檯面下發展。
儘管危險重重,卡斯楚在古巴取得勝利後,革命精神又煥發了生機。反過來,薩爾瓦多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採取高度警戒之姿對抗在西半球的共產主義,以致命武力對付不斷升級的示威活動,示威現場由兼職士兵以及寡頭政治資助組成的「敢死隊」所形成的嶄新惡勢
力,更加大了衝突的規模。整個七○年代,一連串的綁架、失蹤和暗殺,導致了血腥的報復和廣泛的恐怖活動。接著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發生了一場政變。在薩爾瓦多歷史上,政府的強制性變革已經不是第一次,但從未能直接在政策和日常生活方面帶來明顯的變化。即使到了萬聖節,結果仍未明朗。
小海梅有很多話想對他的女兒亞歷珊卓說,她已經在維吉尼亞的福克斯克羅夫特中學(Foxcroft School)唸完高中,希望能夠繼續前往波士頓的大學修讀政治學。小海梅幼年時期就被送往羅德島(Rhode Island)的寄宿學校,在他住那兒的期間,他一直夢想著像祖父詹姆斯一樣回到家鄉種植咖啡。有一天,跟他一樣名叫海梅的父親突然在學校出現,並向兒子解釋由於他失去了視力,需要有人來接管家族企業。小海梅上了費城的華頓商學院的大學。畢業後,他在華爾街工作了幾年,然後回到薩爾瓦多實現父親的期望。
小海梅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個老時鐘,指針來到四點十五分。他坐到打字機前,準備寫信給亞歷珊卓。此時,一輛吉普車和一輛小卡車向他的住處加速駛來,在門前急煞車。身穿員警和陸軍制服的士兵從吉普車中爬出來,清空街道,並用軍用的突擊步槍指揮交通。另一組戴著深色口罩、身穿橄欖色軍服的人馬從皮卡車上跳下,舉著烏茲槍衝了進來。陣陣槍聲擊倒了一名警衛,並在鋼製安全門上炸開一個洞。持槍歹徒衝進房子,經過一個被嚇傻的祕書,然後上樓。
小海梅在辦公室聽到樓下傳來騷動聲時,他的第一個念頭還以為是員警在追捕竊賊。當他聽到樓下傳出槍聲和尖叫聲時,他知道自己弄錯了。八年前,一個恐怖主義集團偽裝成馬路修繕工人,攔下了一輛載著埃內斯托.杜伊納斯(Ernesto Regalado Dueñas)所乘坐的汽車,杜伊納斯是小海梅的表弟。三天後,杜伊納斯的屍體被扔在大街上。小海梅的父親因此讓他買了件防彈背心,至此,恐懼開始與他如影隨形。
小海梅在一陣驚慌失措之下,抓起放在書桌裡的點四五口徑手槍,跑到洗手間躲了起來。他待在裡頭發現自己被困在那裡,手裡拿著手槍感覺就像拿著一個啞鈴。門的另一側傳來一個聲音呼喚著他的名字。小海梅放下了槍,緩緩步出浴室,與頭戴面罩的歹徒面對面。不一會兒,他的頭被套上了頭套,手腕被銬上手銬,一雙看不見的手抓住他的手臂,將他拖下樓梯,經過早已嚇得軟腿的祕書以及殞命的保鏢,然後拖往大街。「告訴我的家人,我毫髮無傷。」小海梅在歹徒的身後哭喊道,接著他臉朝下被扔進尚未熄火的皮卡車後面,在綠色的篷布下,卡車迅速駛離建築物,駛離市區,向西行,朝向曾經被稱為﹁咖啡之鄉﹂的目的地前去。
半個世紀前,通往聖塔安娜(Santa Ana)的道路崎嶇不平,得順著小路蜿蜒而下,才能進入倫帕河谷(Lempa River_)的寬闊盆地。下方的平原上,整齊建築的白色粉刷牆面,在三面環繞著茂密叢林的映襯之下熠熠生輝,紅瓦屋頂在和煦陽光的照射之下烘烤著。隔著一段距離來看,聖塔安娜是整個中美洲最美麗的小鎮──一九二○年代一位曾在此地駐足的美國記者定下的封號。
聖塔安娜在當時稱得上是薩爾瓦多的第二大城市,自一八八○年代開始,它便成為經濟繁榮的中心,至今仍在持續發展中,這都要歸功於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與加州開展的商業活動不斷增加。相較於人們對於一個全球繁榮之城寄予的期望,這個圍繞中央廣場形成的井然有序的城市網絡,似乎顯得「活力不足」,這是因為繁榮的性質並非由此界定。
多數生意是在城鎮邊緣以外、八千英尺高的聖塔安娜火山斜坡上完成的,聖塔安娜火山是薩爾瓦多最高的火山,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座死火山。在廣闊的火山表面上,從山麓一路來到陡峭的火山頂,散布著蓊鬱的綠色咖啡種植園。在收穫季節的每一天,從十一月到隔年二月,成千上萬的人在這些種植園工作,從黎明到黃昏,從早上六點到傍晚,持續採摘咖啡。在工作結束時,驢子背駝著一袋袋飽滿的麻布袋,公牛拖拉著裝載了滿滿紅色成熟咖啡果的運貨馬車,搖搖晃晃地從火山運送下山,途經塵土飛揚的聖塔安娜街道,前往該市眾多咖啡處理廠之一,將新鮮採摘的咖啡果加工成可供出口的咖啡豆。一年之中這個時候最繁忙的街道,有一條狹窄的道路,從城鎮中心向北延伸,穿過一排西班牙橡樹,橡樹的樹枝交錯生長形成了一條深綠色的隧道。在城市郊區,在道路開始從山谷底部爬升之前,稍微向右拐,左側出現了一個名為「三扇門」(Las Tres Puertas)的現代咖啡處理廠的大門。
大門外,運送員領著他們工作的牲畜到接收站,這裡的工作人員迅速將新鮮的咖啡果送入咖啡處理廠。接下來幾天將從咖啡果中萃取出咖啡豆,經過洗淨的程序後,通過水道輸送到日曬廣場,這個廣場就位在處理廠後面的一大片空地。廣場一角,棕色磚塊上塗有醒目的白色線條,畫出約網球場大小的區域,其間還畫上雙走道。
廣場另一側的小高樓上,聳立著一幢優雅的兩層新蓋建築。該建築被視為西班牙殖民復興(Spanish Colonial Revival)風格,一九一五年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之後廣受歡迎。舊金山博覽會(San Francisco fair)為慶祝巴拿馬運河的開通所搭建而成的新式建築,擁有輪廓分明的白牆、寬闊的外部樓梯、圓柱狀入口、紅瓦屋頂和窗。屋內,詹姆斯.希爾那個身材嬌小、擁有一雙黑眼睛的妻子和他們的一大群孩子──十個孩子當中,只有七個倖存──與詹姆斯這個身材矮小,身高六英尺,臉上戴著金屬框眼鏡的英國人同住。自一九二○年起,他替自己建立起「薩爾瓦多咖啡國王」的美名。
這個美名可以說名副其實,但是儘管如此,它還是帶有意想不到的諷刺意味,即其持有者時而為此津津樂道,時而又試圖掩飾。一八七一年,詹姆斯.希爾出生於維多利亞女王區的英格蘭,在曼徹斯特工業區貧民窟長大,曼徹斯特是一個以貧困和污染而聞名的地區。一八八九年,在他前往薩爾瓦多時幾乎默默無名,與咖啡根本沾不上邊,他透過將紡織品賣往國外,藉此逃離曼徹斯特陰鬱的天空,和籠罩在他身上的陰霾。
在許多方面,紡織品生意與咖啡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布料是一種不起眼卻穩定的交易,畢竟它是基本的必需品。相比之下,咖啡卻像是遊走在農業和財務的鋼索上。這些脆弱嬌貴的樹木需要經過多年辛苦勞動和精心照料,才會有豐碩的成果。更糟糕的是,任何咖啡作物的最終價值,完全取決於國際市場的動盪程度,使得咖啡成為當時流行的敘事小說的背景和主題,以及冒險和毀滅的寓言。
然而,詹姆斯.希爾從這個不太可能的開始出發,建立了一個咖啡帝國,包括他的鄰居和聖塔安娜火山的競爭對手在內,許多人開始考慮這個咖啡帝國也許是全薩爾瓦多最好,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事業。詹姆斯.希爾在一九五一年去世時,旗下共掌管了十八個咖啡種植園,提供﹁三扇門﹂處理廠咖啡豆原料,種植面積共有三千英畝,在收成的高峰期雇用了近五千名員工,每年大約產出兩千噸可供出口的咖啡豆,豐收年更獲利高達數十萬美元。儘管令人印象深刻,但詹姆斯.希爾的咖啡帝國的完整覆蓋範圍,無法用英畝、樹木、員工、生產噸數或是獲利金額來計算,它為千里之外成千上萬的咖啡飲用者提供了一個「展示場」──出於某種原因,他們想知道自己所喝的咖啡來自哪裡,以及咖啡豆在當地的生長狀況。
亞瑟.魯爾(Arthur Ruhl)經常四處遊歷。一八九五年,他離開了伊利諾州羅克福德童年時期的家園,前往哈佛。四年後,他在紐約展開記者生涯,因此有機會周遊世界。一九○二年,他在曼哈頓地底進行地鐵的挖掘。一九○八年,他與萊特兄弟一起待在凱蒂霍克(Kitty Hawk)海灘;一九一○年美國獨立日,他在灼熱的雷諾(Reno)見證了傑克.約翰遜(JackJohnson)擊敗了吉姆.傑佛瑞斯(Jim Jeffries)的「拳王奮鬥史」(Great White Hope);一九一四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墨西哥城時,他曾在墨西哥的韋拉克魯茲(Vera-cruz);一九一五年加里波利(Gallipoli)大戰時,他曾到前線;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他早就來到俄羅斯;他從世界各地將他觀察細膩、讓讀者讀來親切的文章投書到《哈潑》(Harper),《科利爾》(Collier)和《世紀》(The Century)。
魯爾的冒險經歷教會他,如果從固定的角度看待一件事,世界並沒有那麼大,而且每天都在縮小。他寫道:「汽車,廣播和報紙集團,更不用說電纜和現代輪船,世界縮小的速度遠超過許多足不出戶的人們所能想像。」他出於個人喜好,喜歡待在擁有舒適的旅店、崇尚運動與健康、舉止良善、擁有乾淨的街道,還有稱職的交通警察的地方,在規範良好的鄉村俱樂部裡喝上一杯雞尾酒,但魯爾並沒有天真地將舒適與進步混為一談。他並不反對改變原則,他只是好奇想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一九二七年的一個早晨,魯爾來到曼哈頓最南端,登上隸屬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大白香蕉船,前往中美洲。他希望前往「美好的哥斯大黎加」(Nice Little CostaRica)、「麻煩的尼加拉瓜」(Troubled Nicaragua)、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和「繁忙的薩爾瓦多」
(Busy Salvador),近距離了解這個「曾為牧區以及父權共和政體」的國家,如何被吸引到
現代世界的潮流中,及其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在這裡無論好壞,美德被以數量(速度、
高度、人口、利潤!)來衡量,高效率(能源、省時、環境衛生和機器的魔力)則被譽 為天才。
亞瑟.魯爾在薩爾瓦多找到了他想要的東西。電話和電力線管道位於﹁嶄新且非常完美的城市街道之下,政府高官承諾高速公路和機場將很快到來;士兵般的員警部隊經過美國人的訓練,令人信服地戴上頭盔和軍用皮帶的裝備。陣容龐大、辛勤工作、種族混雜的農民階級,不像哥斯大黎加那樣「白」與「民主」,也不像瓜地馬拉那樣充斥「印第安人」而難以溝通。
儘管魯爾停留在首都那段期間,覺得自己像是回到了加州南部,但是令他難以忘懷的是他待在「一個大多數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不到半美元的地方」,地下管線上方的嶄新鐵製人孔蓋時常遭到偷盜,並被當成廢棄品出售。在這座城市度過了愉快的幾天之後,他清楚意識到「薩爾瓦多的一切都圍繞著咖啡」。魯爾事先已與當地人聯繫,之後便搭上前往聖塔安娜的火車。
在聖塔安娜火車站迎接他的是詹姆斯.希爾的三個兒子中的其中一個,他最近剛從加州大學返家,開著他父親的車。當他們在「三扇門」停下來時,魯爾步下車,向眼前這位冷靜、精明、文質彬彬的英國人打招呼,這位英國人不僅負責招待魯爾,也向他導覽這個地方。彼時詹姆斯.希爾已近六十歲,他帶著賓客前往緊鄰住處和處理廠的「試驗性種植園」參觀,一邊走一邊用他手上那支粗壯的手杖戳著樹木周圍的黑壤土,一路上用他那獨特的曼徹斯特口音,愉快地談論著咖啡的生活和知識、土壤和樹木、價格和工資、政變與革命、種植園夥伴和「他的工人們」,他將自己在薩爾瓦多四十年來的經驗向魯爾娓娓道來。
參觀結束後,兩人在詹姆斯.希爾以倫敦金融市中心為藍圖所打造的辦公室裡稍作休憩。在輕鬆隨意的氛圍之下,詹姆斯.希爾再次觸及嚴肅的主題:薩爾瓦多正面臨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為確保咖啡產業不受到影響,他已採取重大的應變措施,家族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年輕一代也參與其中,並被寄予厚望。他倆之間的談話宛如在談論生意經,然而當魯爾聆聽著詹姆斯.希爾冷靜地預測薩爾瓦多的未來時,一股不安感油然而生。他不禁感覺到詹姆斯談論的內容,一方面代表了這個世界的變化莫測,另一方面卻也明顯令人感到「古怪」。
詹姆斯.希爾活到了八十歲。他出生於世界首屈一指工業大城的工人階級家庭。在他於一九五一年去世之前,被公認為是最道地的薩爾瓦多人,也是世界上最根深柢固的寡頭統治者之一。當時,曼徹斯特與聖塔安娜已經不像詹姆斯首度離家時那般遙遠。在詹姆斯.希爾活到八十歲的這段歲月中,即從美國內戰結束到冷戰開始之間的幾年中,正如亞瑟.魯爾所觀察到的,世界變得愈來愈小。鐵路、輪船、汽車、飛機、電報、電話、收音機、電影,和其他新穎形式的燃料、電力和治理管轄形式,將曾經彼此孤立的人、事、物匯集在一起,使其不再遙不可及。當前不僅是我們所稱的全球化昭然若揭的時代──同時也是將「全球」一詞首次應用於涵蓋整個地球現象的年代。
更是一個「全球從未有過如此相互聯繫」的時代,「互連」一詞首度被用來描述個體的相互連結本身被更大的體系相互鏈接。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幾十年來全球緊密相連形構了現代世界的基礎。咖啡的歷史,貫穿於一個全球相互連結與轉變的更龐大的故事架構之中。四百年前,喝咖啡不過是鄂圖曼帝國的一種神祕習俗,甚至在英語中找不到與咖啡相對應的字;如今咖啡儼然成為地球上最廣泛使用的字。三百年前,咖啡只在葉門做商業性的種植培育,並只交由一小批商人控制供給。今天,咖啡已經成為七十多個國家,超過兩千五百萬人所種植的經濟作物。兩百年前,咖啡是社會特權階層的一種奢侈享受,咖啡廳成為分享思想、對話、藝術、政治和文化的地方。它是無與倫比的工作提神飲料,每天裝滿全球數十億個咖啡杯,供給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飲用。一百年前,拉丁美洲的種植園主和美國的商人關注低價咖啡帶來的後果,於是開始嘗試教導美國的咖啡飲用者關於咖啡種植的條件及其重要性。如今,咖啡已成為領導公平貿易的產品,相較於其他任何一種商品,我們會更加去思考世界經濟的運作及其應對方式。
基於這些原因,人們常說「咖啡連接了世界」。的確,咖啡從神祕的穆斯林習俗到成為附庸風雅歐洲人的奢侈品,再成為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它的轉變講述了一個關於世界如何形塑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跟隨詹姆斯.希爾從曼徹斯特到聖塔安娜火山,從他的咖啡種植園、處理廠到舊金山的烘焙廠和美國主要咖啡品牌的真空密封罐,再到雜貨鋪、廚房以及全美各個休息室和咖啡館,這一路以來揭示了相隔遙遠的人、地和物,如何愈發準確地以相互連結的關係運行:世界的連結一詞取自近年來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然而這不過是故事的一半。
現代歷史同時朝向兩個方向發展。新的連結孕育了更深一層的新分歧。十九世紀,世界經濟增長了四十四倍。一八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間,世界貿易增長了百分之一千,全世界從未見過如此令人眼花撩亂的財富創造。然而,生活在溫帶氣候和工業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與生活在熱帶氣候和農業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伴隨全球連結的日益緊密而不斷拉大。
一八八○年發展中的工業社會,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區的兩倍;到一九一四年,數字增長了三倍;一九五○年時,數字則擴大到了五倍。世界貧富的劃分與咖啡飲用者和咖啡工人的劃分一致,前者主要集中在工業化的北半球,後者更集中在以農業為主、永遠處於發展中的南半球。咖啡作為世界最貧窮地區最有價值的農產品,在形成這種分化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
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咖啡已經成為一種極具價值的商品。現今每年的出口額超過兩百五十億美元,零售額更是高出許多倍,而這實際上是對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壟斷。
咖啡不僅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也是全球不平等歷史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咖啡不僅「連接了世界」。相反地,它在過去與現在提出了一個難以回答、而且是個既複雜又必然產生的問題:這種透過日常事物與遠在他方的人連結意味著什麼?
推薦序文
你每天手中的咖啡怎麼來的?喝咖啡如何從鄂圖曼帝國的神秘習俗,逐漸轉變為許多人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為什麼咖啡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分別集中分佈在全球(已開發的)「北方」與(開發中的)「南方」?為什麼許多人都希望透過「公平貿易」改善咖啡農的生活?
《咖啡帝國》討論的就是以薩爾瓦多——曾是世界第四大咖啡生產國——為核心的一部盤根錯節的咖啡資本主義史。
1889年,來自曼徹斯特的詹姆斯‧希爾(James Hill,1871-1951)以薩爾瓦多為基地,打造出影響深遠的「咖啡帝國」,也使自己戴上「咖啡國王」的王冠。其家族事業由咖啡往外延伸,成為壟斷多數經濟與政治資源的權力菁英。然而,在咖啡資本主義之下,薩爾瓦多卻陷入極端貧困,五分之四的兒童營養不良。不僅如此,薩爾瓦多還成為美國與古巴的角力場,政治始終動盪不安,並在1980年爆發內戰,一直持續到1992年。
如作者所言,咖啡透過「帝國與奴隸制」來到拉丁美洲,在拉美已有長遠的歷史。詹姆斯‧希爾到達時,薩爾瓦多早已獨立建國,但咖啡的生產依舊緊緊扣連著帝國主義的脈動。《咖啡帝國》描寫了薩爾瓦多政府如何渴望種植並出口咖啡,並以「自由主義改革」為藉口,透過各種法律手段從「落後」的印地安人手中奪走「未開墾的肥沃土地」,並以軍隊鎮壓反抗。馬克思在描寫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時,曾說「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而咖啡資本主義在薩爾瓦多的打造過程也是如此。
在討論薩爾瓦多之前,《咖啡帝國》描寫了曼徹斯特,當時全球「棉花帝國」的工業中心,也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包括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45)在內,許多作品都生動刻畫了曼徹斯特工人的處境。用作者的話來說,當時的曼徹斯特見證了「所有強大的新型治理和技術形式相結合……用來榨取空前數量的艱苦勞動人口」。
為何從曼徹斯特寫起?因為這正是詹姆斯‧希爾成長的地方。他將曼徹斯特的經營管理模式運用在薩爾瓦多的咖啡種植園和咖啡磨坊。本書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描寫他如何透過各種手段,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組織並榨取男工、女工甚至童工的勞動力,讓他們日復一日種植、採摘、篩選和加工。和英國的工廠一樣,薩爾瓦多的咖啡種植園也施行了「任務制度」(計件制);但希爾進一步將工資分為「現金」和「食物」兩個部分,盡可能以提供食物的方式壓低成本並規劃「合理」的工作量(例如一般工人每天能完成兩項「任務」,並得到兩頓食物;若更努力一點,則可完成三項「任務」,從而三餐都有著落)。希爾還在種植園內發行貨幣並當作工資支付給工人,供其在園內的商店消費。而如何讓人心甘情願勞動?答案是飢餓。因此,必須禁止工人取得種植園中一切可以果腹的食物,例如水果和其他豆類植物。希爾甚至為此建立了一支警衛隊,在種植園裡全天候駐守。
但本書並沒有進行簡單的道德譴責,而是將希爾的行動扣連至維多利亞時代的世界觀(如認為「自然界是一台能夠生產機械工作的巨大機器」的「生產力主義」),以更深入理解其行動邏輯。另一方面,工人也不是逆來順受的傀儡,也會發展出抵抗的手段。從曼徹斯特到薩爾瓦多,與嚴酷的工廠制度相伴相生的,還有左翼思想與行動:「為反對以饑餓為基礎的咖啡種植園生產制度,薩爾瓦多產生的人民共產主義的核心論點是,如果做人就是要挨餓,那麼政府的目標應該是供給而不是剝奪,是飽足而不是饑餓。」
晚近越來越多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試圖從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視角書寫「商品史」(commodity history),透過特定商品的起源、生產、貿易與消費來描繪更寬廣的世界圖像,尤其是殖民統治、奴隸制、資本主義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茶、糖、棉花、菸草、咖啡、香料、巧克力等,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題,涉及的學科至少包括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政治經濟學和飲食人類學。2013年出版的《全球史、帝國商品、地方互動》(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文集。
我們也可以將《咖啡帝國》放在這個架構下來閱讀。《咖啡帝國》文筆極為優美,絕不僅僅是堆疊剪裁史料;儘管文字常帶情感,卻未流於浮泛的批判。我相信《咖啡帝國》已經為全球史與商品史的書寫開拓了新的視界。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NT$409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