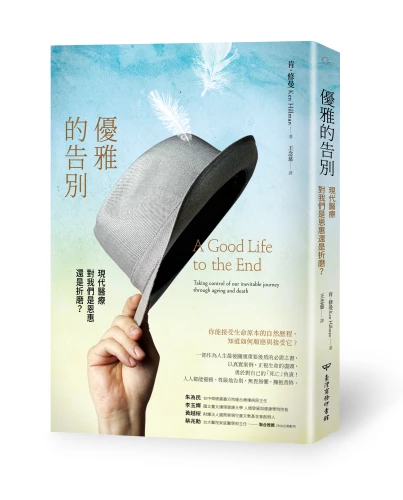優雅的告別:現代醫療對我們是恩惠還是折磨?
商品編號:04000124
優惠活動
購買提醒
本商品為出版已久的書,出版已久的書容易產生些許的黃斑、或有些許瑕疵(例如:壓痕、褪色等),不影響內文閱讀。每本書況不盡相同,請考慮評估後再購買結帳,採取隨機出貨。
如想進一步了解書況詳情,可以來信 cptw1897@gmail.com ,或點擊右上角「 客服 」留言詢問,感謝您支持臺灣商務印書館。
內容簡介
你能接受生命原本的自然歷程,知道如何順應與接受它?
一部作為人生最後關頭重要後盾的必需之書,
以真實案例,正視生命的盡頭,勇於對自己的「死亡」負責!
人人都能優雅、尊嚴地告別,無畏無懼,擁抱善終。
生命自然進程原本就有衰老與死亡,很多人卻無法面對它,更遑論談論它、處理它。當無法預期的意外到來,你的家人必須為你做出決定,卻可能使他們終其一生活在自責的罪惡感中。
反之,亦同樣令人惶恐。
而「守護一絲希望」真的好嗎?要如何有尊嚴的對生命告別? 本書教人正視生命終點面臨的問題,與積極擁有選擇如何渡過餘生的權利,更剖析醫病雙方的整體關聯,讓大眾敢於對生命負責任!
各界專家
朱為民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緩合療護病房主任)
李玉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院長)
黃越綏 (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蔡兆勳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聯合推薦 (依姓名筆劃序)
‧作者修曼醫師以專業角度、平易近人的口吻,提醒讀者生命原有的歷程,充滿人道關懷與省思。
‧以真實故事案例,協助讀者正視生命終結的事實,看清現代醫療的真相!
‧一部面對生命的教戰手冊,從人是如何衰老,到如何選擇好醫者、如何預立遺囑等,再無須逃避。
‧當衰老與死亡難以避免,作者告訴人們如何面對,以保有尊嚴的方式,優雅告別。
「生命之美本來就包涵了死亡。」很多人卻無法了解這一點。身為加護醫學教授的肯‧修曼感受至深。本書就是要告訴我們,其實醫院還可以提供臨終病人更溫和、更符合他們臨終意願的醫療手段,同時賦予我們為所愛或親人提出這些訴求的勇氣。而我們也應轉變對現代醫療的不當期待,與生命自然進程應有的觀點,思考自身對人生終站可以有的「規劃」與態度。
作者以切身的體悟與感慨,提醒讀者大眾正確看待生命的方式,並以生命智慧,調整看待現代醫學的角度,認清它的極限,進一步思考每個人對於衰老與死亡的主動權。
「很多疾病無法單靠醫學來控制或者治癒,
倘若一味仰賴醫學來處置健康的一切毛病,
恐怕會蒙蔽我們看待生老病死的正確觀念,
迷失在永生不朽的想望中。」 ――肯.修曼
作者介紹
肯.修曼 (Ken Hillman)
肯.修曼(Ken Hillman)
加護醫學科醫師,目前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擔任加護醫學教授一職,同時也是辛普森健康服務研究中心(The Simpson Centre for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的主任,以及英厄姆應用醫學研究所(Ingham Institute of Applied Medical Research)的成員。
修曼醫師回到澳洲擔任雪梨利物浦醫院(Liverpool Hospital)加護科主任之前,曾先在雪梨聖文森醫院(St Vincent’s Hospital)受訓,並於倫敦工作六年。他是引進「緊急醫療小組」(Medical Emergency Team,MET)概念的先驅,該理念旨在提升院方對重症患者緊急醫療處置的品質,廣受國際認同,英、美和歐洲多國的多數醫院皆已採納其作法。此外,他對改善垂死病人在急症醫學的照護過程亦不遺餘力。著有《加護病房裡的選擇題:一個30年資深醫師的真實告白》(三采)等。
譯者簡介
王念慈
王念慈
熱愛文字與閱讀,人生中途轉了個彎,從學術臨床走進了天天與文字為伍的譯者世界。享受做中學的翻譯生活,更希望透過文字傳遞正面能量,使世界更美好。
Facebook交流專頁:蔓遊世界www.facebook.com/heyallofu
名人推薦
各界推薦語
每一個人,有一天一定會面臨死亡。差別只是在於,有些人在痛苦中離世,而有些人可以優雅告別。閱讀這本書,相信我們離優雅告別,就更近一點。誠摯推薦。
――朱為民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緩合療護病房主任)
直截了當閱讀衰老與死亡,誠實面對臨終、學習放手,才能優雅告別——
――李玉嬋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 院長)
這本書教人勇敢面對生命的自然歷程!值得一讀!
――黃越綏(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學會面對死亡才能懂得生命,但死亡猶如烈日令人不敢直視。
本書作者透過真實案例,讓我們提早思考要選擇什麼方式退離人生舞台。
――蔡兆勳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理事長)
目錄
前言 | |
第一章 | 我母親人生中的最後六個月 |
第二章 | 衰老是人生必經之途 |
第三章 | 為搶救而搶救 |
第四章 | 晚年跌倒 |
第五章 | 細胞凋亡 |
第六章 | 土撥鼠日 |
第七章 | 認知下降 |
第八章 | 丹妮絲的宣言 |
第九章 | 加護醫學無國界 |
第十章 | 診斷面臨的兩難 |
第十一章 | 衰弱症 |
第十二章 | 要死不容易 |
第十三章 | 生前遺囑 |
第十四章 | 學會放手 |
第十五章 | 無效醫療 |
第十六章 | 加護醫學:人生終點的起站 |
第十七章 | 敲開天堂的門 |
第十八章 | 如何選擇好醫師和好醫院 |
第十九章 | 醫療化的悲歌 |
第二十章 | 衰老和死亡的禁忌話題 |
第二十一章 | 下一步該往哪走? |
致謝 |
試閱
選摘
在仍難以捉摸該如何治療失智症的時刻,我們又該如何對待失智症呢?首先,我們必須坦然接受認知能力衰退是人體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它就跟皮膚會隨著年紀的增長發生變化一樣自然。認清這一點,或許有助你減輕在面對失智症時,常感受到的恥辱感和無助感。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楚跟家人表示,如果有一天失智症嚴重癱瘓了我們正常生活的能力,不想再為了身上其他可治癒的併發症接受積極性治療的意願,尤其是當這些治療手段必須要動用到維生機器才可完成時。
我們還應該更誠實的面對重度失智症的預後和病程,讓病患家屬和其他照護者對患者之後的狀態有更充分的心理準備。即便是重度失智症的患者,他們最多都還可以有一、兩年的日子可活;當然這段日子的長短,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患者本身的健康狀態和照護的品質。
如何給予日益增加的失智症患者和照護者適當的支持,又是另一個有待我們解決的問題。儘管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擁有的鋒芒可能不比找到失智症的療法耀眼,但是它對患者和照護者來說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別是照護者,因為他們的人生常常會被照護工作壓的喘不過氣來。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可以把投注在找尋失智症療法的部分巨額資金轉移,用於尋覓支持患者和照護者的最有效方法,或許就可以讓他們在有生之年過著更有尊嚴和有品質的生活。此舉可以更加確保整個社會能一起均攤失智症患者的照護負擔,不會讓這個重擔全都落在區區幾個人的肩頭上。大眾都很捨得為了最新醫療科技和藥物砸下大錢,相較之下那些專職照護體弱老人的照護者薪資就非常低廉,甚至,假如家屬本身就是照護者的話,他們還連一毛錢都沒有。
喬治和他妻子洛琳的狀況就清楚描繪出了失智症照護者面臨的困境。喬治六十七歲,自從洛琳開始出現早期的失智症症狀後,他已經整整照顧了她十一個年頭。過去十二個月,洛琳為了脫離危及生命的險境陸續住了四次醫院,兩次是因為尿道感染,另外兩次則是肺炎。每一次,喬治都及時發現了洛琳身上的早期感染症狀,並趕緊將她送往醫院。每一次,腎臟專科醫師和胸腔內科醫師都對洛琳做出了正確診治,並讓她住院觀察。老實說,這種「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的治病方式並不困難,他們只需要稍加問診,並給予洛琳靜脈輸液和抗生素即可;如何依據患者的整體狀態給予「最恰當」的醫療處置才是比較困難的部分,而這一點許多醫學教科書裡都沒有提到。
洛琳有重度的失智症;她不能自己洗澡或著衣,不能在沒有輔助的情況下走路、吃飯必須要有人餵、大小便失禁,也無法說出有意義的話語。縱使有好心的社工協助喬治照護洛琳的部分工作,但他卻遲遲申請不到使用社區照護(community care)的資格,而且洛琳的狀況還符合四間政府照護機構的申請標準。喬治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在打理這件事,在這個過程中甚至還發現了很多跟他有著相同處境的朋友。
喬治後來雖然終於排上了其中兩家機構的等候名單,但距離獲得正式幫助的日子似乎遙遙無期;至於另外兩家機構則只願意提供他零星的居家照護協助。喬治甚至有考慮過把洛琳送往安養院照護,但這也必須等待長達九個月的時間(除非你有額外給付一筆費用給機構,就可以將等待的時間縮短為三個月),而且喬治其實還沒有做好把妻子送到那裡的心理準備。
喬治絕大多數照護妻子的技巧都是因為妻子多次因感染住院,跟醫院的照護人員學來的。比方說拍痰、伸展四肢肌肉、如何有效餵食、如何避免褥瘡,還有如何及早發現感染的前兆等。現在喬治六十八歲了,但他儼然已經失去了享受自己人生的權利。過去三年,他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被迫待在家裡,寸步不離的照顧著洛琳,直到半年前有一些社工到家裡協助他部分照護洛琳的工作,他才稍稍有一點喘息的空間。他發現自己在做某些照護洛琳的工作越來越吃力,譬如把洛琳抱去浴室洗澡、替她更換尿布,還有幫她穿衣服。另外,他也覺得很寂寞,因為洛琳的狀況讓家裡鮮少有親朋好友來作客。
我是在洛琳第五次住院的時候見到喬治的。當時靜脈輸液和抗生素無法將洛琳的病況穩定下來,她的血壓突然下降,喬治連忙按下病房的急救鈴求救。急救過後,普通病房的醫療人員要我到洛琳的病房評估一下她的狀況,看看她是否可以轉入加護病房。抵達洛琳的病房時,我看到了在病床邊心慌意亂的喬治,普通病房的護士則快步朝我走來,跟我交代洛琳的病況。了解洛琳的狀況後,我同意將洛琳轉入加護病房,但是在治療的方式上需要有一些限制,即:我們會持續給予她輸液和抗生素,但是不會用任何維生機器支持她的生命徵象,或是用藥物來維持她的血壓。
在親屬室裡,我跟喬治說明,重度失智症是一種致命的疾病,現在他的妻子正走向人生的終點。聽完我說的話,喬治非常震驚,他說:「從來沒有人跟我說過這些!」於是,我試著向他解釋,階段性醫療和照護常會讓人無法認清患者的真實處境,所以有時候醫療人員也很難告訴他這方面的資訊。
結束這場對話後,我們相約隔天再詳細討論其他的事情。翌日,喬治帶著他的三個孩子一起來討論洛琳的後續安排。我先跟他的女兒和兩個兒子說明洛琳的狀態,然後告訴他們;他們的母親已經病入膏肓,所以我們不會再去監測她的生命徵象,而且我們不再會限制洛琳的訪客次數和人數,所以洛琳的每一位親友都能夠好好地跟她道別。
不過,就在我們討論完洛琳後續安排的兩個小時後,洛琳就辭世了。喬治那時候剛好返家補眠,我請護士撥個電話給喬治,告訴他,他的妻子病況突然惡化要他來醫院一趟,但不要跟他說洛琳已經死了。這是病人死亡時的既定程序,我們不會在電話中直接告訴對方病人的死訊。或許是因為這種重大的訊息不適合透過冷冰冰的電話傳達,就連警察在通報死訊的時候,通常也都會親自到府說明。
完成交班的巡房後,我步出醫院,站在我的車子旁邊準備返家,碰巧看到喬治匆忙趕到醫院。看他臉上的表情,我想他肯定非常焦慮又困惑;因為洛琳的狀態已經差的不能再差了,在他離開的這短短兩小時內,還能惡化到什麼程度。有一瞬間,我曾考慮是不是該跟著他一起回到加護病房,在那裡陪著他,替他分擔一些喪妻之痛。但後來我決定不要這麼做,因為先前我就已經跟喬治說過這一切都是人生的必經之途,此刻我更應該給喬治和他的家人一點空間,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他們深愛的親人。
推薦序文
前言
有人警告過我,沒有人會想要讀一本繞著老化和死亡主題打轉的書,因為這樣的內容太過晦暗、令人抑鬱。然而,正視死亡這件事,其實可以讓我們更從容的面對它;我反倒覺得,等到自己變得體弱多病、垂垂老矣,心中卻還抱持著不切實際的想望才是更加令人抑鬱的處境。及早了解我們真實的健康狀態,不僅有助我們掌握自己的人生,還能讓我們適時做出相關的安排。
事先設想好自己面臨人生終點的原則,亦可免除家屬在這方面的負擔,否則在某些情況下(例如你腦部不幸受到重創,餘生註定都要仰賴他人照料),家屬恐怕就得被迫替你做出攸關生死的決定。面臨這類決定時家屬往往會陷入兩難,因為他們可能既不願意因放棄治療背上不肖親屬的罪名,也不願意同意治療而讓至親承受不必要的苦痛。簡而言之,不論最終家屬做出了哪一種決定,他們的心中或許都難逃罪惡感的折磨。
在討論這類主題時,有時候也會有人提出「永不放棄希望」之類的主張,說什麼諸如「倘若你不懷抱希望,又怎麼能奢求希望降臨」的老套說詞。老實說,這樣積極正面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前提是這份希望必須合乎情理,不然不切實際的希冀根本毫無建設性可言。舉例來說,如果我們鼓勵大眾去「對抗」末期癌症,那麼萬一他們抗癌失敗,可能就會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換而言之,儘管保持積極進取的態度很好,但盲目否定現實的情況絕對無法讓你從中獲得任何好處。
在這本書裡,我就是要請大家學會用理性的悲觀,而非用虛妄的樂觀,去看待事情。坦白說,悲觀在當代並非是主流的看事角度。撇開永遠抱持樂觀主義的經濟學家不說,政客和媒體為了讓事實以比較賞心悅目的面貌呈現,大多會用樂觀扭曲真相;就連醫學界也常以「報喜不報憂」的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加深大眾對醫療的錯誤期待。沒錯,我們看事的角度確實不必全然悲觀,但是在看待這些經過樂觀包裝的事物時,我們心中對它們仍要存有合理的懷疑。
許多西方國家的人,人生的最後幾天都是在加護病房(又稱ICU)裡度過;而我這個加護醫學科醫師,主要服務的單位自然就是加護病房。若要回顧我和加護病房結下的緣分,得從一九八年代初說起。早年我在倫敦教學醫院執業,當時加護醫學背後所蘊藏的邏輯和科學能量就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個時候在加護病房裡,我不但能應用各種機器測量和監測患者的生理指標,還可以利用機器延續患者的生命;在那裡,所有的生命彷彿都可以獲得一線生機。即使是今日,我仍然會因從死神手中搶下病人的性命感到歡欣,不過同時,我也學會欣賞善終的美好,理解讓患者在免於受苦、保有尊嚴的情況下離世,對認同這個理念的家屬是多麼大的寬慰。
基本上,在加護病房裡工作的日子,我幾乎天天都會聽到一起工作的同仁悄聲說:「以後請千萬別讓我受這種苦。」
我會開始關注「臨終」這個議題,是由於醫院和加護病房病人的族群不斷出現變化。過去送到加護病房的病人除了年齡層相對較低,他們身上危及性命的病症(如重度感染和創傷),在我們的專業協助下,往往也很有機會在各種繁複的手術過後,度過險境、重拾健康。反觀今天,加護病房裡照顧的病人,大多是心臟和神經動了大手術,需要仰賴維生機器輔助幾天,好從手術中恢復的高齡患者。我們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把這些患有老化疾病的高齡病人納為加護病房的照護對象。因為既然我們的機器可以將年輕的傷患從致命的疾病中救出,又有什麼理由不把它們應用在年長者身上?我們曾經想過,把年紀超過七十歲,心臟動了大手術的病人納入加護病房的照護對象到底恰不恰當。但事實證明,把這些病患送入加護病房照料,可以大大提升他們的術後存活率。因此,我們又陸續把八十歲、九十歲的病人納入照護的對象,甚至我還曾照顧著幾位百歲人瑞級的病人。
年齡跟存活率並沒有絕對的關連性,但是這當中有一項顯而易見的事實,過去我們一直忽略了。儘管現在許多被送入加護病房的年長病患,其病症(例如創傷和感染)和年紀較輕的病患相去不遠,且都是在重大手術後需要特別照護的病人,然而,與年輕病患不同的是,這些年長病患的預後狀況往往不是單純由這些病症的狀況所決定,而是由那些早就潛藏在他們體內的老化慢性病所主導,如冠狀動脈疾病、糖尿病、失智症和骨關節炎等。這些慢性病痛會讓身體器官全面的衰退,進而使年長者比較容易得到感染、癌症等疾病,甚至是增加了他們跌倒的機會。雖然目前為止我們尚未把這些因素歸納成一套具體的評分標準,但上述的種種因素的確都增加了年長患者在加護病房裡面臨的風險。漸漸地,在加護病房裡,我們越來越常用「衰弱症」(frailty)這類名詞形容這些年長者的狀態。事實上,最近我們才慢慢了解,這些年長者在住進醫院後,狀態之所以會每況愈下,完全是因為他們早已步入行將就木、壽命將盡的人生階段。認知到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類病患需要的醫療處置和一般患者截然不同。我認為,與其讓這些患者把人生的最後幾天或是幾週,虛擲在加護病房裡,醫療人員倒不如用更真誠的態度去向病患及其家屬說明他們的健康狀態,讓他們有機會自己決定度過人生最後一段路的方式。
這本書要說的老化和死亡不會如迪士尼童話那般美好,因為它既不會告訴你該如何長命百歲,也不會告訴你該如何治癒癌症或避免失智症找上門;相反的,我會透過文字直截了當地把老化如實呈現在你眼前,告訴你,老化和死亡之間有著多麼不容忽視的關聯性和必然性。一如死亡,我們也必須理解和接受老化。我明白要你接受不熟悉的事情很難,所以這本書會盡可能讓你對它們有一定的認識。
書中我分享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只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病人姓名或是某部分的臨床細節有稍做更動。這些故事並非是什麼我個人的特別經歷,它們每天幾乎都會在世界各地的醫院裡輪番上演。實際上,醫院並不擅長處理生命即將燃盡的病人,因為它們本身的存在就是為了救治傷患,而非放棄傷患。因此,我絕不會對我的同儕做出任何批判,畢竟,我們醫師在受訓時被灌輸的觀念就是「竭盡所能的拯救性命」,而不是將死亡視為是一個理所當然、不可避免的人生階段。在我的職涯中,我一直覺得能和許多無私又有能力的醫師、護士和相關醫療人員共事,相當與有榮焉。他們不僅擁有處理身體特定病痛的專業技能,更總是對病人充滿關愛。
縱然如此,但從大面向來看,現在走向極致分工的醫療體制,卻讓我們慢慢失去了可以為病人把關整體健康狀況的「通才型醫師」;即便有部分家庭醫師仍會對醫院提供給患者的醫療照護心存疑慮,認為病人的整體狀況不適合這類醫療方式,可是面對大醫院裡的專科醫師和精密醫療科技,這些家庭醫師大多沒有那份為病人提出心中質疑的自信。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強化大眾和社區對年長者的照護服務,如此一來,臨終的虛弱長者才有機會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度過餘日。
一九五年代是我們從出生到離世的人生路上,跟醫學越來越密不可分的分界點。當時準備分娩的婦女會被送入醫院,在那裡她們只能全然聽從醫療人員的指示,然後在幾乎沒有任何止痛的情況下,緊張不安的張開雙腿,奮力生出腹中的嬰兒;待她們的嬰兒呱呱墜地後,護理人員立刻就會把嬰兒被送入育嬰室,集中照料一大群的新生兒。至於孩子的爸爸,當時不只完全無法參與自己太太分娩的過程,還僅能偶爾隔著育嬰室的玻璃窗匆匆看自己的孩子一眼。
隨著時間推進,這些出生在戰後嬰兒潮的世代也開始生兒育女,同時親眼見證自己的雙親在醫院臨終前因為過度醫療蒙受的苦痛,遺憾的是,在這段過程中,不論是病人或是家屬依舊很少向院方表達過自己的意見。此刻,這本書就是要號召大眾正視這個問題,並鼓勵大家挺身主宰自己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