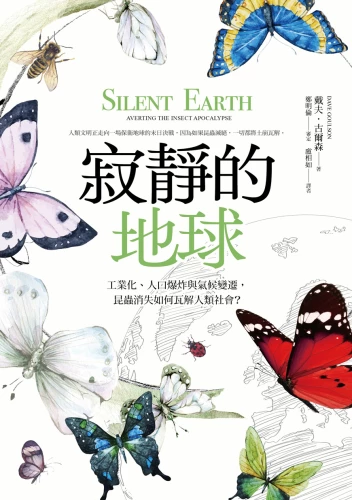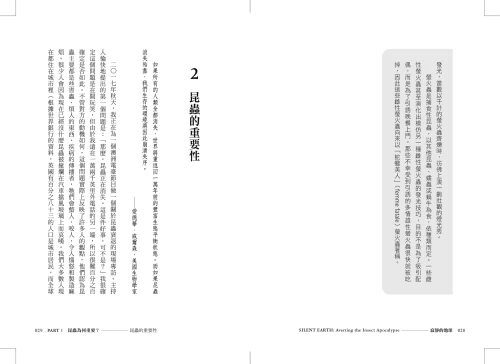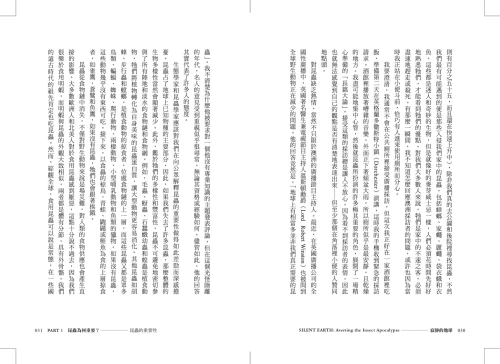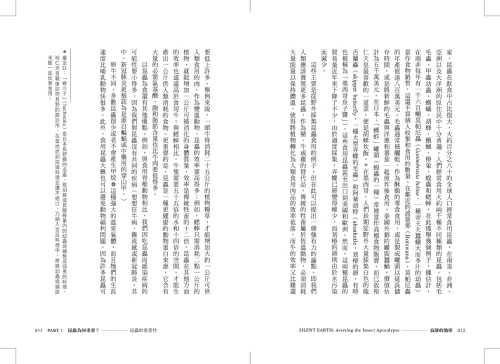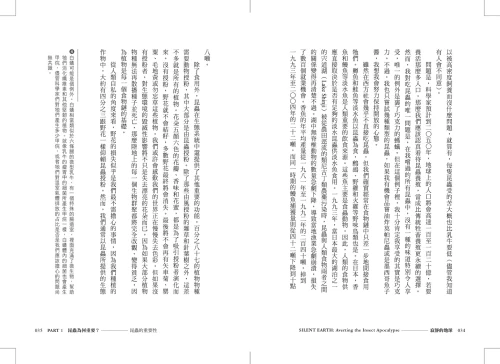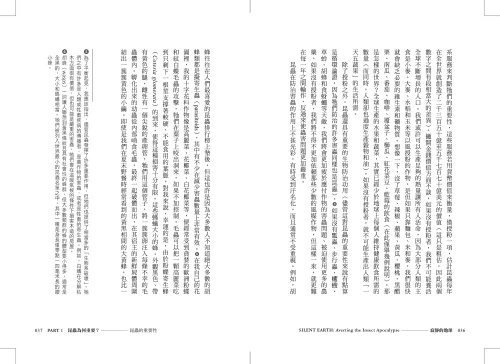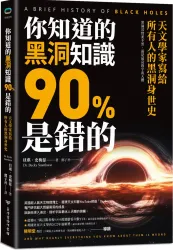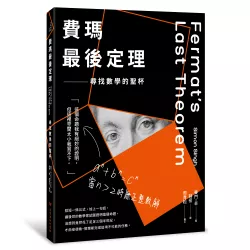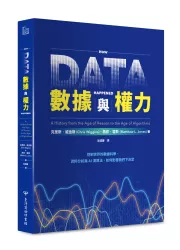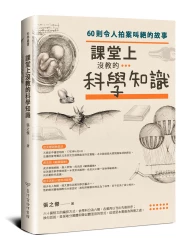內容簡介
榮獲《泰晤士報》和《每日電訊報》二○二一年精選讀物
敲響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的響亮警鐘
「人類正走向一場環保的末日決戰,如果昆蟲滅絕,一切都將土崩瓦解。」──戴夫.古爾森
六十年前,《寂靜的春天》出版,成為促成全球禁用DDT的曠日鉅作,這場人類環保史上最大的一場勝利,卻帶來往後長年的悲劇──當科學家們認為勝利已定,誰能想像接下來幾十年新問世的殺蟲劑帶來的問題,又有多麼龐大?
一九八八年,由一群昆蟲學家組成的德國克里菲德業餘昆蟲學會(Krefeld Society),不斷監視著六十三個自然保留區中的昆蟲體重,並在二○一五年將資料委由戴夫.古爾森分析。結果,戴夫.古爾森非常驚恐的發現,在這二十七年中,昆蟲數量減少了76%──在二○一五年的夏天甚至高達82%,而這僅僅限於昆蟲學會監視的自然保護區。
昆蟲的消逝,勢必帶來人類的滅絕
人類社會,比你我想像的還更依賴昆蟲
昆蟲雖然在人類社會時常引發厭惡或排斥的聲浪,但實際上人類社會處處都需要仰賴昆蟲:在人類栽種馴化的一百一十三種作物中,有高達八十三種必須仰賴昆蟲授粉,昆蟲成為延續人類糧食生產的重要命脈;昆蟲作為食物鏈最底層,成為維持生態多樣性的最基礎群體;在防治害蟲上,昆蟲作為天生的競爭者,可以免去殺蟲劑帶來的無差別傷害;而在生態分解上,儘管化學藥劑占了重要角色,但人類社會至今仍仰賴昆蟲在土壤、廚餘、糞便中發揮其用。
然而,當昆蟲生態豐富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如乾草場、沼澤地、石楠地和熱帶雨林,已經遭推土機剷平、焚燒,或因犁地而被大規模破壞;當無差別使用殺蟲劑成為了常態,昆蟲減少所帶來的影響將會愈來愈明顯──在某些果園,昆蟲消失,農民被迫以人工授粉,導致了糧食生產量大幅減少;蜂巢崩潰綜合症造成蜜蜂數量銳減,造成果園農園的歉收。當昆蟲消失的未來近在眼前,誰能想像當昆蟲紛紛消失後,地球生態將快速瓦解、氣候變遷與土壤侵蝕將更為嚴重?當雨林與森林缺乏昆蟲授粉、缺乏營養的土壤,使得凝聚森林的輕薄土層破碎瓦解,溫室氣體從土壤湧出的未來將勢不可擋──而這一切,都將使地球能養活的人口數量急劇下降。
二○三○年,氣候難民將擠滿世界各大城鎮
二○四○年,世界主要糧食供應將快速瓦解
拯救昆蟲,是挽回這一切的關鍵!
儘管昆蟲消失已成定局,但至今地球上仍有不少昆蟲與物種並未瓦解,起而行動,永遠不會嫌時間太晚!戴夫.古爾森從挽救昆蟲的角度切入,結合了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減少之間的聯繫,揭露了昆蟲數量下跌帶來的災難,並分析對地球與人類的有害影響。對戴夫.古爾森而言,挽回這一切並沒有人類想像的困難──一切只在於人類在不在意,因為拯救昆蟲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拯救人類。
作者介紹
戴夫.古爾森
戴夫.古爾森(Dave Goulson)
英國昆蟲學家、科普作家,英國皇家昆蟲學會及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員。他曾在牛津大學研習生物學,現為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生物學教授。戴夫.古爾森是一名享譽全球的生物研究學家,尤其以在昆蟲研究方面的成就知名,投入全球昆蟲數量研究長達三十年。
戴夫.古爾森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環境保護人士,其成功促使歐盟立法禁止全歐使用新菸鹼類殺蟲劑,並於二○○六年成立熊蜂保育信託,投身具有開創性的保育工作,使他獲得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研究委員會頒以「年度社會改革者」榮銜。
譯者簡介
盧相如/鄭明倫(審定者)
審定者簡介
鄭明倫
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碩士,美國堪薩斯大學生態暨演化生物學系博士。現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物學組。跟本書的作者一樣,從小就喜歡昆蟲,有個與昆蟲為伍的人生,後來也體悟到還有太多值得用人生去做的事,包含審訂這本書在內,這也是人人行動救未來的一部分。
譯者簡介
盧相如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目前為自由譯者,喜歡閱讀小說。譯作有《吃動物》、《咖啡帝國》、《凌空之夢:1974,我在世貿雙塔上走鋼索》、《告訴你有多好吃:我的第一本美食寫作書》、《滾貓不生苔:貓咪教你的人生哲學》、《大草原的奇蹟》等。
名人推薦
聯名推薦(依來函順序刊登)
黃仕傑/科普作家、節目主持人
黃一峯/金鼎獎科普作家、生態教育工作者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番紅花/作家
柯心平/臺灣昆蟲館館長
這是一本關於「好事」的書:昆蟲默默地為生態系做的「好事」、人類肆無忌憚地對地球幹的「好事」、科學家如何「好(ㄏㄠˋ)事」地研究這些「好事」,以及每個人為了自己和子孫都該盡力達成的「好事」。
──鄭明倫/審定者、美國堪薩斯大學生態暨演化生物學系博士
「昆蟲需要你的幫助?」這句話聽起來似乎有點矛盾,甚至許多人可能覺得討人厭的昆蟲消失最好。但你可能沒有意識到昆蟲消失後的問題,單就人們喜愛的水果來說,如果昆蟲消失了,沒有牠們幫忙,果樹也無法結果,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這本書從昆蟲的世界出發,以各種故事闡述牠們的重要性以及面臨的威脅,希望在未來,我們還能和昆蟲和平共處,並攜手合作打造一個舒適而豐美的生活圈。
──黃一峯/金鼎獎科普作家、生態教育工作者
六十年前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開啟了人們重視化學殺蟲劑對生態的危害,希望這本《寂靜的地球》能讓人們擔負起對未來所有生命該有的責任。在自然活動中常玩的生態遊戲有一種相當受歡迎的「生命之網」,織起生命之網的,並不是人類,我們只是網上一股絲線,但由於我們濫伐雨林或滅絕了物種,而讓這張網產生破洞,我們也身受其害,因為各種生命之間是環環相扣的。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目錄
前言:與昆蟲為伍的人生
Part 1:昆蟲為何重要?
1. 昆蟲簡史
2. 昆蟲的重要性
3. 昆蟲大驚奇
Part 2:昆蟲的衰退
4. 昆蟲衰退的證據
5. 基線偏移
Part 3:昆蟲衰退的原因
6. 失去家園
7. 遭受汙染的土地
8. 除草劑
9. 綠色沙漠
10. 潘朵拉的盒子
11. 山雨欲來
12. 閃閃發光的地球
13. 外來物種
14. 已知的和未知的未知數
15. 千刀萬剮
Part 4:何去何從
16. 前途未卜
Part 5:下一步該怎麼做?
17. 提高意識
18. 綠化我們的城市
19. 農業的未來
20. 自然無處不在
21. 行動救家園
致謝
延伸閱讀
試閱
二○一七年秋天,我正在為一個澳洲電臺節目做一個關於昆蟲衰退的現場專訪。主持人愉快地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那麼,昆蟲正在消失。這是件好事,可不是?」我很確定這個問題是在開玩笑,但由於我遠在一萬兩千英里外電話的另一端,所以很難百分之百確定是否如此。不管對方的動機如何,這個問題實際上反映了許多人的觀點,他們認為昆蟲主要都是些害蟲、煩人的東西、疾病的傳播者,牠們會螫人、咬人、令人惱怒和製造麻煩。很少人會因為現在已經沒什麼昆蟲被撞爛在汽車擋風玻璃上而哀嘆。我們大多數人現在都住在城市裡(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英國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口是城市居民,而全球則有百分之五十五,而且還在快速上升中),除非我們真的去公園和後院裡尋找昆蟲,不然我們最有可能遇到的便是那些入侵我們家中的昆蟲,包括蟑螂、家蠅、麗蠅、袋衣蛾和衣魚。這些都是迷人和奇妙的生物,但是就像好的麥芽威士忌一樣,人們必須花時間先好好地熟悉牠們,才能看到牠們的優點。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牠們是家中的不速之客,必須盡可能迅速地趕走或殺死。有那麼一瞬間,我不知道怎麼回應澳洲採訪者的問題,或許也因為當時我正站在小便斗前,恰巧有人剛進來使用廁所而分心。
我要澄清,我通常不會在公共廁所裡接受廣播採訪,但這次我正好在一家酒館裡吃飯,準備第二天在英格蘭多徹斯特小鎮(Dorchester)演講,這時我的手機收到緊急的採訪請求。酒館裡播放著嘈雜的音樂,外面正下著傾盆大雨,所以廁所似乎是最安靜,且乾燥的地方。我盡可能地集中我的心智,然後就昆蟲所扮演的許多極其重要的角色,展開了一場精心準備的「長篇大論」。接受這類的採訪總是讓人不放心,因為看不到採訪者的表情,因此也就無法感覺到自己的觀點是否有清楚地表達出來——但至少那個在角落裡小便的人贊同地點頭。
對昆蟲缺乏熱情,當然不只限於澳洲的廣播節目主持人。最近,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全國性廣播中,英國著名醫生兼電視節目主持人溫斯頓勳爵(Lord Robert Winston)也被問到全球野生動物正在減少的問題。他的回答竟然是,「地球上有相當多並非我們真正需要的昆蟲」。我不清楚為什麼他被要求對一個他沒有專業知識的主題發表評論,但在這個光怪陸離的年代,名人的意見受到重視似乎很尋常,無論其資格或經驗如何。儘管如此,他的回答其實代表了許多人的態度。
生態學家和昆蟲學家應該對我們在向公眾解釋昆蟲的重要性做得如此差勁而深感擔憂。昆蟲占了地球上已知物種的主要部分,因此,如果我們失去了許多昆蟲,那麼整體的生物多樣性當然會顯著減少。此外,鑑於牠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昆蟲不可避免地密切參與了所有陸地和淡水的食物鏈和食物網。例如,毛蟲、蚜蟲、石蠶蛾幼蟲和蝗蟲是植食動物(Herbivore),牠們將植物轉化為自身美味的昆蟲蛋白質,讓大型動物更容易消化。其他昆蟲如胡蜂、步行蟲和螳螂,作為植食動物的掠食者,位處食物鏈的上一層。這些昆蟲又都是眾多鳥類、蝙蝠、蜘蛛、爬行動物、兩棲動物、小型哺乳動物和魚類的獵物。如果沒有昆蟲,這些動物幾乎沒有東西可吃。接下來,以食蟲的椋鳥、青蛙、鼩鼱或鮭魚為食的上層掠食者,如雀鷹、蒼鷺和魚鷹,如果沒有昆蟲,牠們也會跟著挨餓。
昆蟲從食物鏈中的喪失,不僅對野生動物來說是場災難,對人類的食物供應也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大多數歐洲人和北美人對於食用昆蟲感到厭惡,這點十分說不過去,因為我們很樂於食用明蝦,而明蝦與昆蟲的外觀大致相似,兩者都是體有分節、具有外骨骼。我們的遠古時代祖先肯定也吃昆蟲。然而,綜觀全球,食用昆蟲可以說是常態,在一些國家,昆蟲在飲食中占很大比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全球人口經常食用昆蟲,在南美、非洲和亞洲以及大洋洲的原住民中十分普遍。人們經常食用大約兩千種不同種類的昆蟲,包括毛毛蟲、甲蟲幼蟲、螞蟻、胡蜂、蛾蛹、椿象、蝗蟲和蟋蟀。在此僅舉幾個例子,據估計,在南非每年有一千六百噸莫帕尼蟲(Gonimbrasia belina,一種帝王天蠶蛾大而多汁的幼蟲)當作食物銷售,這還不算個人收集和食用的數量。在鄰近的波劄那(Botswana),莫帕尼蟲的年產值達八百萬美元。毛蟲通常被曬乾,作為酥脆的零食食用;或是製成罐頭以延長儲存時間,或是將新鮮的毛蟲與洋蔥和番茄一起煎炸後食用。泰國出產的罐裝蠶蛹,價值估計為五千萬美元。在日本,「螞蚱」罐頭(蝗蟲的一種)常被當作高檔食物販賣,而已故裕仁天皇最喜歡的一道菜,便是胡蜂大米飯。在墨西哥,長期以來,人們從野外大量採集白色的龍舌蘭蟲(skipper butterfly,一種大型弄蝶的毛蟲)和阿華胡特(ahuahutle,划椿的卵,有時也被稱為「墨西哥魚子醬」),這些食用昆蟲甚至出口到美國和歐洲。然而,這兩種昆蟲的貿易量近年來下降了不少,由於過度採集,弄蝶已經變得稀少,而划椿的卵則由於水污染而減少。
這些主要是從野外採集昆蟲食用的例子,但在此可以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論點,即我們人類應該養殖更多昆蟲,作為豬、牛或雞的替代品。傳統的牲畜屬於恆溫動物,必須消耗大量能量以保持體溫,使得將植物轉化為人類食物的效率低落,而牛的效率又比雞還要低上許多。舉例來說,一頭牛得消耗二十五公斤的植物糧草,才能增加大約一公斤可供人類食用的肉。作為變溫動物,昆蟲的效率要高得多:例如,蟋蟀只需消耗二點一公斤的植物,就能增加一公斤可被消化的身體質量,效率是傳統牲畜的十二倍。昆蟲在其他方面的效率也遠遠高於食用牛:與蟋蟀相比,乳牛需要五十五倍的水和十四倍的空間,才能生產出一公斤供人類消耗的食物。更重要的是,昆蟲是一種更健康的動物蛋白來源,它含有大量的必需氨基酸,其飽和脂肪含量也比牛肉要低得多。
以昆蟲為食還有其他優點。例如,與實用脊椎動物相比,我們因吃昆蟲而感染疾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為我們與昆蟲沒有共同的疾病。(想想狂牛病、雞流感或新冠肺炎,其中,新冠肺炎更被認為是源自蝙蝠或中醫用的穿山甲。)
與牛不同,多數昆蟲很少或者不會產生甲烷 這種強大的溫室氣體,而且牠們的生長速度比哺乳動物快很多。而且食用昆蟲,大概也可以避免動物福利問題,因為許多昆蟲可以被高密度飼養而沒什麼問題,就算有,昆蟲受苦的能力大概也比乳牛要低(儘管我知道有人會不同意)。
問題是,科學家預計到二○五○年,地球上的人口將會高達一百至一百二十億,若要養活那麼多人口,那麼我們應該認真看待昆蟲養殖,當成比傳統牲畜養殖更永續的選擇。然而,我對吃昆蟲的唯一問題是,在我嚐過的所有昆蟲中,沒有一種的味道特別令人感到愉快,唯一的例外是裹了巧克力的螞蟻。但在這個例子裡,我十分肯定我享受的其實是巧克力。不過,我也只嘗試幾種類型的昆蟲,如果我有機會品嘗油炸莫帕尼蟲或是墨西哥魚子醬,我想我會努力保持開放的心態。
雖然在西方社會幾乎不直接吃昆蟲,但我們確實經常在食物鏈中只差一步地間接食用牠們。鱒魚和鮭魚等淡水魚以昆蟲為食,鷓鴣、野雞和火雞等野味鳥類也是。在日本,香魚和鰻魚等淡水魚是人類重要的飲食來源。這些魚主要是食蟲動物,因此,人類的食物供應直接取決於是否有足夠的淡水昆蟲供淡水魚食用。一九九三年,當日本最大的湖泊之一的宍道湖(Lake Shinji)被從農田逕流的類尼古丁類農藥污染時,昆蟲與人類食物兩者之間的關係變得再清楚不過。湖中無脊椎動物的數量急劇下降,導致當地漁業急劇崩潰,損失了數百個就業機會。香魚的年平均產量從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二年的二百四十噸,掉到一九九三年至二○○四年的二十二噸,而同一時期的鰻魚捕獲量則從四十二噸下降到十點八噸。
除了食用外,昆蟲在生態系統中還提供了其他重要的功能。百分之八十七的植物物種需要動物授粉,其中大部分是由昆蟲授粉。這差不多就是所有的植物,除了那些由風授粉的雜草和針葉樹之外。花朵五顏六色的花瓣、香味和花蜜,都是為了吸引授粉者演化而來。沒有授粉,野花就不會結籽,多數野花最終將會消失。最後將不會再有矢車菊、罌粟、毛地黃或勿忘草這些植物。我們或許會感歎我們的世界正在慢慢失去色彩,但如果沒有了授粉者,對生態環境的毀滅性影響,將不只是失去漂亮的花朵而已。因為如果大部分植物物種無法再散播種子並死亡,那麼陸地上的每一個生物群聚都將完全改觀、變得貧乏,因為植物是每一個食物鏈的基礎。
從人類自私的角度來看,野花的損失似乎是我們最不需擔心的事情,因為我們種植的作物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的作物跟野花一樣仰賴昆蟲授粉。然而,我們通常以昆蟲所提供的生態系服務來判斷牠們的重要性,這些服務若用貨幣價值來衡量,僅授粉一項,估計昆蟲每年在全世界就創造了二千三百五十億至五千七百七十億美元的價值(這只是粗估,因此兩個數字之間有段相當大的差異)。撇開金錢價值方面不談,如果沒有授粉者,我們不可能養活全球不斷增長的人口。我們或許可以生產足夠的熱量讓所有人活命,因為大部分人類的主食是小麥、大麥、水稻和玉米等以風授粉的作物,是但如果只靠麵包、米和麥,我們很快就會缺乏必要的維生素和礦物質。想像一下,沒了草莓、辣椒、蘋果、黃瓜、櫻桃、黑醋栗、南瓜、番茄、咖啡、覆盆子、櫛瓜、紅花菜豆、藍莓的飲食(在此僅舉幾例說明),那是怎樣的世界?全球生產的水果和蔬菜,其實已經少於地球上每個人維持健康飲食所需的數量(而同時,人類卻也過度生產穀物和油)。如果沒有授粉者,就不可能生產出人類「一天五蔬果」的生活所需。
除了授粉之外,昆蟲還具有重要的生物防治功用(儘管這對昆蟲的重要性來說有點算是循環論證,因為牠們防治的許多害蟲同樣也是昆蟲)。 儘管如此,如果沒有瓢蟲、步行蟲、蠼螋、草蛉、胡蜂和食蚜蠅等天敵,我們將會更加疲於應付作物的害蟲問題、被迫使用更多的殺蟲劑。如果沒有授粉者,我們將不得不更加依賴那些少數的風媒作物,但這樣一來,就更難在每一年之間輪作,反過來使蟲害問題更加嚴重。
昆蟲在防治害蟲的作用上不甚光彩,有時受到汙名化,而且通常不受重視。例如,胡蜂往往在人們最喜愛的昆蟲排行榜上墊後,但這也許是因為大多數人不知道絕大多數的胡蜂種類都是擬寄生蟲(parasitoid),其中有不少在減少害蟲數量上非常有效。 在我自己的花園裡,我的十字花科作物像是高麗菜、花椰菜、白花椰菜等,便經常受到貪婪的歐洲粉蝶和紅白蝶毛蟲的攻擊,牠們在葉子上咬出洞來,如果不加控制,毛蟲可以把一顆高麗菜吃到只剩下一根莖支撐著較硬、不能食用的葉脈。對我來說,幸運的是,由於粉蝶寄生蜂(Cotesia glomerata)的到來,使得這種損害十分有限。這些螞蟻大小的胡蜂,外觀黑色、帶有黃色的腿,雌性有一個尖銳的產卵管,牠們用這個管子,將一簇簇卵注入每條不幸的毛蟲體內。孵化出來的幼蟲從內部啃食毛蟲,最終一起破體而出,在其宿主的新鮮屍體周圍結出一簇簇黃色的小繭。即使是我們在夏末野餐時經常看到的黃黑相間的大黃蜂,也比一般人知道的要有用得多。牠們既是野花的授粉者,也是蚜蟲和毛蟲等農作物害蟲的貪婪掠食者,也許我們不應該吝嗇,讓牠們吃下一兩塊我們的食物。
昆蟲在控制不受歡迎或入侵性植物方面也很有價值,如澳洲的刺梨仙人掌(prickly pear cactus)。一九○○年代,來自美洲乾旱地區的刺梨仙人掌被引入澳洲,作為牲畜的藩籬。在我看來,這些植物很可怕,因為牠們長滿了鋒利的倒刺,要是被這些倒刺刺到非常痛苦,而且很難從肉上拔除——我曾經在西班牙研究長腳蜂時掉進刺梨樹叢中——所以選擇以此類植物作為藩籬似乎有些奇怪。而且這類植物不會沿著直線生長,而是長得到處都是,很快便會失控,在澳洲東北部的昆士蘭,刺梨仙人掌覆蓋了四萬平方公里,形成難以穿透的帶刺灌木。一九二五年,來自南美的灰褐色仙人掌飛蛾(Cactoblastis cactorum)被引進,在極短時間內幾乎吃光了所有的仙人掌。
昆蟲甚至還密切參與了有機物的分解,如落葉、木材、屍體和動物糞便。這在大自然中是極其重要的工作,因為可以回收有機物的養分,使這些養分再次用於植物生長。大多數分解者從未受注目。例如,在花園裡的土壤中(特別是你的堆肥,如果你有的話),幾乎一定含有無數的跳蟲(Collembola)。這些微小、原始的昆蟲近親,通常不到一毫米長,牠們以利用彈器(furcula),將自己彈射到空中逃避掠食者的聰明伎倆而得名。跳蟲的彈器通常收平於腹部下方,當遇上緊急狀況發生,牠們會用彈器將自己彈離掠食動物約一百毫米遠。這支微不足道的跳高大軍,牠們從事一項重要的工作,便是啃食有機物中的微小碎片,幫助把牠們分解成更小的碎片,然後進一步被細菌分解,使其釋放出的營養物質可供植物使用。跳蟲是健康土壤中一個重要卻被忽視的組成分子。有些體型較圓潤的種類更是出奇的可愛,就像是胖嘟嘟的綿羊(稍加想像的話)。
這群分解者或許很少被注意到,但如果少了牠們,生態界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澳洲的牛農在二○世紀中期就發現了這一點。在世界各地多數地區,昆蟲大軍爭相爭奪牛糞,所以牛糞不會留存太久。在幾秒鐘,最多幾分鐘之內,草地上的一坨牛糞便會引來第一批糞蠅和糞金龜,牠們被微風中飄來的誘人氣味所吸引。糞蠅產的卵很快就孵化成蛆,然後吞噬腐爛、富含細菌的有機物。糞蠅大約在三週內便可以完成整個生命史。有些糞金龜的祖先是水棲性,*成蟲在新鮮的糞水中,用著如槳一般的腿泅泳。許多糞金龜將牠們的卵產在糞便中,而另一些則在糞便下的土壤中掘穴,並將一些糞便封存其中供後代食用。另有一些糞金龜會將糞球滾離糞堆數公尺遠,希望躲開成群的昆蟲。掠食性地隱翅蟲和步行蟲也來到糞堆,捕食食糞的昆蟲;烏鴉和戴勝等鳥類則被吸引來探尋昆蟲的蠐螬。而糞便中大量的昆蟲不斷挖洞,使糞便的內部逐漸暴露於空氣中,加速糞便乾燥,最終碎裂成細小粉末,成功使糞便的營養物質再循環。
除了釋放營養物質外,昆蟲對糞便的高效處理,還為農民提供了第二項有價值的服務:牠們在清除牲畜的腸道寄生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寄生蟲的蟲卵透過糞便,從受感染的動物體內排出,污染草地並被另一頭牛或羊攝取。但昆蟲透過掩埋和吃掉糞便,很快地就能處理掉這些寄生蟲卵。諷刺的是,現在給牛做的寄生蟲治療,反而使牠們的糞便對昆蟲有毒,因此減緩了糞便的循環利用,加劇了本應被治療的牲畜寄生蟲問題。
相比之下,十九世紀澳洲的第一批牛農所面臨的問題是,沒有任何本地昆蟲能處理溼答答的牛糞。早已適應乾旱環境的澳洲哺乳動物,像是袋鼠和袋熊等有袋類動物,牠們產生的糞便與牛隻有很大的不同:有袋類動物產出的糞便較為堅硬,呈顆粒狀。從歷史上來看,澳洲的糞金龜已經適應了以這種糞便為食,卻幾乎完全無法處理第一批歐洲定居者引進的牛隻所產生的糞便。結果,牛糞需要多年才能被分解,累積的量讓牧草長不出來,使得放牧場留給牲畜的草愈來愈少。假設每頭牛每天產生大約十二坨牛糞,到一九五○年代,澳洲被牛糞覆蓋的面積估計每年增加兩千平方公里。
一九六○年代,來自匈牙利的新移民喬治.博內米薩(George Bornemissza)博士,提出引進糞金龜以處理牛糞問題的解方,澳洲糞金龜計畫因此誕生。博內米薩接下來花了二十年時間,在世界各地尋找適合引進澳洲的糞金龜物種,尤其是南非的糞金龜,因為兩地氣候相似。在此之前,人類刻意將非本地物種引入澳洲的一些做法都造成可怕的後果:例如,來自南美洲的海蟾蜍(cane toad),當初被引進澳洲為的是幫助防治甘蔗害蟲,沒想到牠們卻引發了一場大災難,直到今日,澳洲的海蟾蜍數量估計有兩億隻。海蟾蜍除了不吃牠們原本要消滅的害蟲之外,其他什麼都吃。相較之下,引進的糞金龜的計畫,則顯著地成功。總結而論,澳洲共引進了二十三種不同的糞金龜,引進的標準是根據牠們清除糞便的速度來選擇,而且這些不同種類的糞金龜,能夠在澳洲不同的氣候區繁衍成長。如今,多虧了這些糞金龜,澳洲的牛糞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便能夠神奇地消失。
其他號稱自然界殯葬業者的昆蟲,在處理屍體方面也具有同樣的高效率。反吐麗蠅 (Calliphora vomitoria)和麗蠅(Lucilia sericata)能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動物死後幾分鐘內找到屍體,產下大量的卵。卵在數小時內孵化成一隻隻蠕動的蛆,在其他昆蟲趕來之前競相嚙食屍體。牠們的親戚,肉蠅(Sarcophagidae),在這場競賽之中占有優勢,因為牠們能夠直接產出蛆蟲,完全跳過了卵的階段。蒼蠅和糞金龜在處理糞便方面相互競爭,在此情況下,埋葬蟲儘管趕來的速度較慢,但牠們會同時吃掉動物的屍體和發育中的蛆。埋葬蟲會把小動物的屍體拖到地底,接著在上面產卵,然後留下來照顧牠們的後代,保護牠們不受其他埋葬蟲的傷害,如果牠們判斷產下的後代過多,剩餘的食物不足以供應,還會選擇剔除並吃掉一些後代。不同的昆蟲種類抵達的順序以及牠們的生長的速度,在任何一個特定的環境條件之下都是可預測的,甚至當死因可疑時,法醫昆蟲學家(forensic entomologist)也可以藉此判斷人類屍體的大約死亡時間。
除此之外,穴居、土居的昆蟲還能夠幫助翻動土壤;螞蟻協助散播種子,牠們會將種子帶回蟻巢食用,但往往在途中還落一些種子,這些種子便有機會發芽;蠶蛾吐絲;蜜蜂提供給我們蜂蜜。總結而論,僅僅在美國,昆蟲每年提供的生態系服務至少價值五百七十億美元,但是這個計算不太具有意義,因為昆蟲的價值,如同受人尊敬的善心生物學家威爾森曾經說過,沒有了牠們,「環境將崩壞,陷入混亂」,數十億人將因此挨餓。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要付出什麼行動?
許多昆蟲的作用重大,但我們根本不知道大多數昆蟲在做什麼。在現存可能有五百萬種昆蟲中,其中有五分之四的種類人類尚未為其命名,遑論研究牠們扮演的生態角色。近年來,製藥公司已經開始進行「生物勘探」,他們在不同的昆蟲中發現了無窮無盡的化合物,並發現了許多具有潛在醫療用途的新化合物,包括可能幫助我們解決抗生素的抗藥性細菌的新抗菌化合物,以及抗凝血劑、血管擴張劑、麻醉劑和抗組胺劑等化合物。每一個滅絕的昆蟲物種,都意味著一個潛在的藥物寶庫將永遠消失。
正如保育家奧爾多.里奧波德(Aldo Leopold)所說,「修補的首要原則,便是保護所有的螺絲釘。」在構成大多數生態群落的數千種生物裡,彼此之間眾多的相互作用所知甚少,因此我們不能說我們「需要」或「不需要」哪些昆蟲。對作物授粉的研究發現,大多數授粉往往是由少數物種完成,但隨著時間進展,當有更多物種出現時,授粉將變得更可靠,更有彈性。畢竟,不同昆蟲物種的數量每年都會自然波動;有些昆蟲可能在春寒料峭、大雨或乾旱中應付自如,因此,在某一年完成大部分授粉工作的昆蟲,可能不是接下來一年或十年內的主要授粉者。僅僅依靠一種昆蟲授粉,如養殖的蜜蜂,是一種愚蠢的策略,因為如果養殖蜜蜂發生任何問題,將沒有任何備案。 伴隨氣候的變化,授粉者的群聚也會跟著變化,今天看起來不重要的物種很可能成為明日的主要授粉者。昆蟲所做的其他工作也可如此觀之,有越多不同類的昆蟲可用,我們就越有機會將這些重要的工作延續到不確定的未來。
美國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有一個著名的比喻,他把生態群落中物種的消失,比喻成從飛機機翼上隨機彈出的鉚釘。去掉一個或兩個,飛機可能會沒事。去掉十個、二十個或五十個,在某個我們完全無法預測的時刻,將會導致災難性的失事,飛機就會從天上掉下來。昆蟲是維持生態系統運作的鉚釘。我們距離災難性的邊緣有多近,人類尚不得而知。然而,在一些地方,卻已經遭遇了昆蟲消失的後果。在中國西南部的部分地區,因為幾乎沒有授粉者,農民們被迫為他們的蘋果和梨子進行人工授粉,否則他們的作物將無法結果;在孟加拉,我看到農民替瓜果進行人工授粉;巴西部分地區農民也指出他們必須替百香果進行人工授粉。此外,世界各地許多研究發現,包括加拿大的藍莓、巴西的腰果,以及肯亞的法國豆,由於授粉昆蟲數量不足,密集耕作地區的昆蟲授粉作物產量較低,而靠近原生林地區或其他野生動物豐富地區的農場產量則較高,因為這些地區仍保有較多的授粉昆蟲。在英國,最近一項關於加拉蘋果(Gala)和考克斯蘋果(Cox)生產的研究發現,由於授粉不足,水果的品質受到影響,農民目前正逐漸損失大約六百萬英鎊的潛在收入。顯然,在世界許多地方,我們正處在或已經因為授粉者不足而必須限制作物產量的節骨眼上。如果連我們的農作物都得努力吸引足夠的授粉者,那麼野花更可能如此;如果野花因授粉不足而進一步減少,那麼這意味著倖存的授粉者的食物就會更加短缺。一些科學家推測,這可能會引發「滅絕漩渦」,在這個漩渦中,花朵和授粉者的數量,將會以螺旋式的方式下降,從而雙雙滅絕。
在很大程度上,昆蟲所做的工作並未被人類社會所注意,牠們的付出,甚至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大多數畜牧業者幾乎沒有考慮過糞金龜的重要性,直到最近仍鮮少有耕作者採取任何措施,來促使授粉者增加或保護作物害蟲的天敵。就像澳洲的牛農或孟加拉的瓜農一樣,只有當昆蟲不再幫助我們時,我們才會被迫注意到嚴重性。在一切為時已晚之前,我們應當開始感激昆蟲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才是明智之舉。
推薦序文
與昆蟲為伍的人生
我從小就對昆蟲著迷。記得我五、六歲時,發現了一隻黃黑色條紋相間的毛毛蟲,牠在學校操場邊緣的柏油路縫隙中長出來的雜草上覓食。我把牠們收集起來,放進沒吃完的午餐盒裡,然後把牠們帶回家。在父母的協助下,我找到更多合適的葉子餵牠們,最終毛蟲蛻變成洋紅色和黑色相間的漂亮的蛾(某些歐洲的讀者可能會認出牠們是朱砂蛾[Tyria jacobaeae])。對那時我來說,這就像是某種魔法,且至今依然如此。我因此迷上了昆蟲。
從那時起,童年時期的愛好成為我現在謀生的技能。十幾歲時,每到週末和假期,我總是拿著網子追捕蝴蝶,用「糖餌」誘捕飛蛾,挖陷阱捕捉甲蟲。我從專門的郵購商那裡買來外國飛蛾的卵,看著牠們長成外觀有著五顏六色的毛毛蟲,最終變成巨大、光彩奪目的蛾:有來自印度的長尾水青蛾(Actias luna),來自馬達加斯加、會突然露出假眼(false eye)的孔雀蛾(Saturnia pyri),以及世界上最大、來自東南亞的巨大的深棕色皇蛾(Attacus atlas)。當我取得牛津大學的錄取通知時,很自然地選擇進入生物學系就讀,後來我在牛津布魯克斯大學以蝴蝶生態學研究攻讀博士,這所大學位在牛津東部的一座山上,相當不顯眼。之後,我設法取得了各種不同的研究職位:首先,我回到牛津大學,研究番死蟲(Xestobium rufovillosum)奇特的交配行為,接著在牛津的一個政府實驗室,研究如何透過向農作物噴灑病毒來控制蛾類害蟲。由於這份工作要殺死昆蟲,讓我感到十分厭惡,所以當我取得南安普頓大學(Southampton University)生物系的終身教職時,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我在南安普頓大學開始專門研究熊蜂(bumblebees),那是最吸引我的昆蟲,而且牠們彼此間有著激烈的競爭。我對熊蜂如何選擇要造訪的花朵感興趣,並花了五年時間來解開牠們如何透過嗅聞微弱足跡,得知一朵花是否剛被其他熊蜂捷足先登。我了解到在熊蜂看似笨拙的泰迪熊外表下,牠們其實很聰明,堪稱是昆蟲界的天才,牠們能夠導航並記住地標和花叢的位置,有效率地萃取隱藏在精緻花朵中的報償,並生活在密語和弒君都很普遍的複雜社會群落裡。與牠們相比,我年輕時追逐的蝴蝶現在看來成了美麗卻單純的生物。
為了追尋昆蟲,我有幸環遊世界,從巴塔哥尼亞的沙漠到紐西蘭峽灣的冰峰,甚至是不丹潮濕蓊鬱的山脈,都曾經有我踏遍過的足跡。我曾在婆羅洲觀看成群的鳥翼蝶(birdwing butterflies)在一條河流的泥灘上吮吸著礦物質;在泰國的沼澤地,看著成千上萬的螢火蟲在夜間齊爍著牠們發光的尾部;在我位於蘇塞克斯郡(Sussex County)家中的花園裡,我也花了無數時間趴在地上觀看蝗蟲求偶和擊退對手,看著蠼螋(earwig)照顧牠們的孩子,看螞蟻從蚜蟲(aphid)身上擠出蜜汁,看切葉蜂(leafcutter bee)剪下樹葉來做巢。
儘管我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樂趣,卻對於這些生物的數目正在日益衰退的事感到憂心忡忡。打從我第一次在學校操場上採集那些毛毛蟲以來,距今已經五十載,在那之後的每一年,蝴蝶和熊蜂的數目都慢慢地在減少,所有使世界運轉的這些小生物幾乎都在減少。這些迷人而美麗的生物正在消失,日復一日,一隻接著一隻,無論是螞蟻或蜜蜂。儘管估算結果各異,準確度也並不一致,但在這五十年間,昆蟲的數量似乎已經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或者更多。這方面的科學證據每年都在增加,愈來愈多的研究報告發表指出,北美的帝王蝶(Danaus plexippus)族群趨於崩潰,德國的森林和草原的昆蟲逐漸消亡,還有英國的熊蜂和食蚜蠅(hoverfly)分布範圍巨幅縮減。
一九六三年,在我出生前兩年,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在她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中就曾警告我們,我們在對地球施以可怕的破壞。要是她看見地球現在這幅模樣,恐怕也不免要痛心落淚。昆蟲生態豐富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如乾草場、沼澤地、石楠荒原和熱帶雨林,已經遭推土機剷平、焚燒,或因犁地而被大規模破壞。她所強調的殺蟲劑和化肥的問題,已經變得更加劇烈,現今估計每年有三百萬噸的殺蟲劑噴灑在世界各地。其中一些新的殺蟲劑對昆蟲的毒害,比起卡森的年代的任何殺蟲劑要大上數以千倍。土壤已經退化,河流被淤泥堵塞,並遭化學藥劑污染。在她的年代尚未出現的氣候變遷現象,現在有可能進一步蹂躪我們受困的星球。這些變化都發生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而且不斷加劇中。
對熱愛這些小生物並重視牠們的人來說,昆蟲的減少讓我們十分痛心疾首,但同時這也威脅到人類的福祉,因為我們需要昆蟲為作物授粉,處理糞便、落葉和屍體的循環,保持土壤健康、控制害蟲數目,還有其他不計其數的理由。許多大型動物,如鳥類、魚類和蛙類都以昆蟲為食。野花依靠牠們來授粉。隨著昆蟲的數目變得愈來愈少,我們的世界將慢慢陷入停滯,因為沒有牠們,世界便無法運轉。正如瑞秋.卡森所說:「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對自然的戰爭不可避免地也是對自己的戰爭。」
我現在花費許多時間試圖說服其他人喜歡並關愛昆蟲,或者至少尊重牠們所做的一切重要事物。當然,這也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希望你們能像我一樣看待昆蟲,牠們美麗、令人驚奇、有時極其古怪,有時險惡惱人,但總是令人驚歎,值得我們敬佩。你將會對牠們的一些奇特的習性、生活史和行為感到驚訝,而這使得牠們成為科幻小說家在現世孜孜矻矻發揮想像力的來源。在本書中,除了探索昆蟲的世界、牠們的進化史、牠們的重要性以及牠們所面臨的眾多威脅,我也簡要地介紹一些我最喜歡的昆蟲的生活,當成章節之間的串場。
儘管時間緊迫,但仍為時不晚。我們的昆蟲需要你的幫助。大多數昆蟲還沒有滅絕,只要我們給牠們一些空間,牠們便能迅速恢復,因為昆蟲繁殖快速。昆蟲就生活在我們的周遭:無論是花園、公園、農田、在我們腳下的土壤中,甚至在城市人行道的縫隙中,所以人人都能一起照顧牠們,確保這些重要的生物不會消失。儘管面對許多山雨欲來的環境問題,我們或許感到無能為力,但我們仍然可以採取簡單的措施來復育昆蟲。
我們需要深刻的改變。我們應該邀請更多的昆蟲進入我們的花園和公園,將我們的城市,以及交錯連結的路邊草皮、鐵路邊坡和環形道,變成一個充滿花朵、無農藥的棲息地網絡。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斷裂的食物供應系統,減少食物浪費和肉類消費,為大自然留出大片不被過度生產的土地。我們也要發展真正的永續農業,專注於與大自然合作生產對我們有益的食物,而不是在大片、貧瘠、滿是農藥和化肥的單一栽種區之中種植經濟作物。我們能夠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來推動這些改變:購買和食用當地、當季、有機生產的水果和蔬菜;種植我們自己的食物;投票給那些認真對待環境的政治人物;教育我們的孩子,讓他們知道好好地照顧地球,是件刻不容緩的事。
想像一下,在未來,我們的城市和城鎮鬱鬱蔥蔥,處處是野花、結實纍纍的樹木、綠化的屋頂和綠色的植生牆;孩子們可以從小聽著蝗蟲的叫聲、鳴鳥的歌唱、熊蜂飛過的嗡嗡聲,看著蝴蝶閃耀的彩翼長大。城市周圍環繞著充滿生物多樣性的小型農場,生產由各種野生昆蟲授粉的健康蔬果,由天敵大軍控制著蟲害,由無數善於掘土的生物維持土壤的健康和碳庫(carbon stock)儲存。在離城鎮更遠的地方,新的野化計畫提供了休閒的機會,讓人們得以探索河狸築壩所形成的充滿蜻蜓和食蚜蠅的濕地、長滿野花的草地和成片的林地,都充滿生命力。這看起來也許像是一個幻想,但是在我們的地球上,仍有足夠的空間讓所有人都過著富足的生活,吃得好與健康,並擁有一個孕育著各種生命、蓬勃盎然的綠色星球。我們只是必須學會融入自然,而不是與它漸行漸遠。多虧昆蟲這樣的小生物使我們共存的世界運轉著,所以第一步便是從關懷昆蟲做起。
NT$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