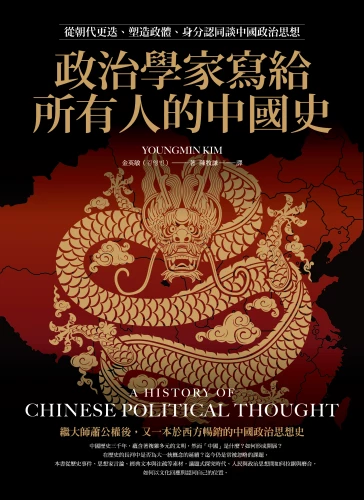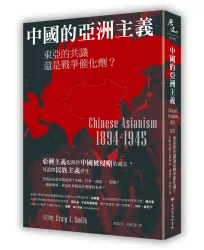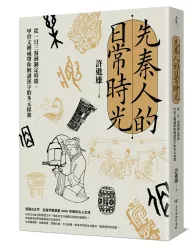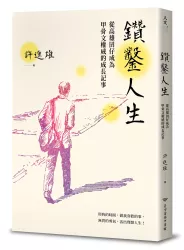內容簡介
★繼大師蕭公權後,又一本於西方暢銷的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國歷史三千年,蘊含著複雜多元的文明,然而「中國」是什麼?如何形成開展?在歷史的長河中是否為大一統概念的延續?迄今仍是常被忽略的課題。本書從歷史事件、思想家言論、經典文本與注疏等素材,議題式探究時代、人民與政治思想間如何拉鋸與磨合,如何以文化回應與認同自己的位置。
「中國」是國家?抑或地理名詞?
「專制」與「大一統」並非認識中國史的絕佳視角?
在朝代更迭間,人們該如何應對新變革?新舊王朝的思想觀是否有延續?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作為全球大國迅速崛起,然而全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忽視或過度簡化塑造中國的漫長歷史,以及在國際轉型上的複雜思想和理想。在大眾的認知中,中國一直是作為單一且固定的國家存在,然金英敏教授提供了新的視角,探問中國歷朝的政治秩序和思想,真的超過兩千年從未改變?
每個朝代的開展或能視為一個嶄新秩序,
更是思想家與傳統道德互動、形塑敘事視角的契機。
作者循著中國歷史的進程,以影響中國深遠的孔子時代為開篇,結束在當今中國對全球新秩序的探索。分別探討各朝代不同時期的政治特徵與社會願景,用跨領域的研究思路,從文學、經濟、藝術、哲學等方面挖掘線索,傾聽人民的聲音、釐清政府的態度,再賦予獨到的論述,並運用豐富的學術研究來佐證,深刻地挑戰了中國政治思想的傳統觀念。
★作者給讀者的建議★
學習中國政治思想除了能讓視野更為開闊之外,究竟還能從中學到什麼?有的人可能免不了想問:我們到底能學到哪些教訓?是能理解善治的本質,還是能了解當今的問題?有的人甚至會說,只要我們將中國政治思想加以更新,以適當的方法重新構想,便有望能為今日的世界找到政治秩序的理想。我的心願相較之下簡單許多:中國政治思想本身就富饒興味。這並不是說中國政治思想能夠為善治的本質給出絕對的答案,而是我們能從中找到豐富的資源,以此反思自己關心的政治議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該忽視觀念跟歷史現實之間的聯繫,以此照見當時時空中的政治經驗。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專文導讀
「本書以長時段通史維度書寫中國政治思想的同時,亦強調超越國族主義史觀的一元論述。……雖以書寫中國政治思想為綱,卻不以目的論式的敘事強調政治思想對於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延續性影響,而更加側重中國政治思想的內在多元性。」
作者介紹
金英敏(김영민)
首爾大學政治系教授,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東亞思想史研究博士,曾在布林莫爾大學( Bryn Mawr College)任教,長期致力於東亞政治思想史、比較政治思想史相關研究,特別著力於中國帝國晚期思想史、韓國思想史、新儒家思想。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思想史與政治思想,著作除本書外,另有《韓國婦女與儒家思想》(Woman and Confucianism in Chôson Korea)。
目錄
推薦語
導讀 從政治思想重訪「中國」的多元面貌/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本書提及的朝代
前言
導論 如何理解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國是什麼?
研究中國性的各種取徑
威權政府的詮釋
儒家的概念
類型分析取徑與行動者中心的取徑
本書敘事手法
幾條主要軸線
第一章 文明禮俗社會——影響歷代思潮的孔子
從神權政體到文明禮俗社會
禮與認知能動性
禮與情感能動性
政治菁英的形成
小政府、小國家
第二章 政治社會——戰國思想對禮的論辯
政治社會的概念
相互競爭的理念
墨子:平等分配資源
荀子:欲望與資源要供需平衡
老子:君主需無為而治
韓非子:自利是為改善處境
楊朱:以自我為中心
孟子:普遍人性具有道德
莊子:以審美角度看待世事萬物
第三章 國家——從地方政權到中央集權
涉外關係:秦漢與外族的二元關係形成
商鞅變法:與人民溝通,強化軍事實力
賈誼〈過秦論〉:秦朝為何二世亡?
鹽鐵之議:賢良文學之士與御史大夫的辯論
第四章 貴族社會——被動地遵守階級文化的唐朝
新的歷史情境
唐代的秩序
多元包容的中國性
超越華夷之分的皇帝
宗教寬容
開放的仕途
唐律賦予各階層的框架
國家與貴族的共生關係
唐代秩序的衰頹
「被動從眾」作為政治意識形態
皇帝要有為?無為?
貴族獨有的文化素養
佛教與國家深度融合
韓愈提倡復古
〈鶯鶯傳〉反映唐代社會秩序
社會的個人、內心的自我
第五章 形上共和國——宋朝士人的道學思想
如何定義南宋的中國性?
新型菁英的出現
道學與形上共和國
形上共和國——人人平等,菁英群體可施展政治抱負
第六章 混一天下——中國士人在蒙古帝國中的身分認同
朝貢貿易體制
對蒙古統治的回應
耶律楚材:促使元朝轉型的關鍵人物
趙蒼雲與趙孟頫:用藝術表現政治觀點
馬致遠:《漢宮秋》中的王昭君
馬致遠翻轉中國中心論
第七章 獨裁體制——帝制晚期君主的絕對權力如何產生?
中國歷史中的君權
理解明代專制統治的不同取徑
另闢研究明朝的取徑
王廷相的唯物哲學
第八章 是公民社會還是政治有機體?——帝制晚期的政治角色思辨
中國的公民社會之辯
《大學》八條目的追求
理解八條目的不同取徑
作為政治語彙與政治綱領的八條目
政治有機體的兩種理念
對君主的勸諫:集合政治體的各部門團結合作
對平民的建議:王陽明的政治思想
第九章 帝國——多元族群國家的統治者與人民
清代統治者的政治身分認同
實學:與道學對立的百科全書式學問
善治與地方自治
中國脈絡下的西化
結語 從大脈絡思考中國
在近代早期東亞競逐核心地位
在現代東亞競逐核心地位
在當代世界競逐核心地位
徵引文獻
試閱
第一章 文明禮俗社會——影響歷代思潮的孔子
要講述中國政治思想史,從孔子(前五五一?—前四七九?)開始可說是極為合理,畢竟長久以來,世人視孔子為儒家的創始人,是中華文化的完美典範。但是,如果用這種框架理解孔子,首先會出現的問題是,孔子即便是在他的時代中也是難以分類的人物,不論我們怎麼定義「儒家」,在孔子的時代都不存在這樣的講法。即便我們現在常將古代的中國思想家分類成所謂儒家、道家或法家,但這些分類其實是後世才創造的標籤;在孔子的年代,還沒有形成什麼樣的學術思潮,也沒有組織成什麼運動,沒有辦法辨認所謂的「儒家」出來。實情是:孔子只是一位導師,一生桃李滿門,那些身懷抱負的學生求教於孔子,想要了解世界的秩序;要直到漢代時,中央政府才開始遵奉孔子的教誨,拿孔教做為自我辯護的手段之一。
從漢代開始,日與俱增的經注學者投入闡釋孔子的教誨。某種程度上來說,孔子之所以能活過漫長的歷史延續至今,必須仰賴各式各樣調和的過程,倚靠數世紀以來衛道之士的辯護,乃至經注學者的努力——光是「如何讓孔子之後的人能接受的方式發聲」這個議題,便會佔去剩下思想史的一大半。因此,孔子承載了重要的文化意涵,接下來的世世代代都把自己安排世界秩序的想法安放到孔子身上,歷史中會出現各種方法來解讀孔子的思想也就不奇怪了。當我們想在中國傳統中考察各種詮釋孔子的脈絡時,這種層累的現象使得任務變得更為棘手。
有些現代的學者認為,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沒有留下任何可信的史料、不足以重建當時的思想世界;他們對孔子思想的詮釋常常有時空錯置之處,可能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然而,數十年來,情形已經有所轉變,像尤銳及羅泰等許多學者的研究便在此列。最主要的差異在於,相較於蕭公權視孔子為那個時代突然乍現的突破,尤銳將孔子置於時代脈絡中,說明他的思想並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在東周的文化氛圍和知識發展中演變而生。例如,《左傳》逐年紀錄了西元前七七二年至前四六八年的政治活動,而尤銳便特別分析此書,以此重建春秋時期的思想史。所以,當時確實還有更早的傳統存在,很可能啟發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有了羅泰、尤銳等學者的描繪,我們知道孔子其實是時代中廣大思想浪潮的一部分,當時的各家學說努力避免政治秩序走向崩解,試圖重塑傳承而下的思想資源,以恢復社會安定。這種脈絡考察的視角挑戰了一些舊說,例如有些主張將孔子視為「復古論者」(traditionalist),表示他想要恢復早期周代的禮制。這類錯誤的假說或研究取徑,其實都對研究孔子思想造成了阻礙。
孔子一生大多在東周的前半段度過。東周之名源自西元前七七〇年的事件,當時周朝統治者的權力受到限制,失去原本的領土,不得已必須東移到黃河上的首都(位在今日洛陽一帶),而傳統的分期將東周分為春秋及戰國兩個部分。《左傳》中成公十三年的一句話,恰如其分地呈現了當時的時代氛圍:「國家的重大事務,在祭祀與戰爭。」(《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考古發現表示,孔子時代的社會大量使用青銅製作武器和禮器,反映了當時社會這兩項核心的特徵——祭祀與戰爭,兩者都是組織群體生活的有力方式。想要發動戰爭,青銅武器不可或缺,而戰爭確實也是建立政治秩序的典型手段;然而,因為暴力的代價高昂,而且使用越多收效越少,不可能不斷地使用暴力。因此,政治菁英勢必得找到代價較小的方法來建立政治秩序,而宗教儀式則能以合理的代價來建立政治菁英企求的那種政治秩序。政治權力透過宗教儀式一再地神聖化,給予統治菁英神聖合法性,從而透過這種方式維繫政權,而政治秩序一旦有了信仰加持、成為某種現實,自視與秩序合而為一的政治菁英,便不再需要訴諸永無休止的戰爭。要想知道在古代中國這種政治動態如何開展,我們應該要考察上古中國的朝代更迭。
對多數中國史學者來說,夏、商、周王朝代表了三個最早前後存在的朝代,構成了中國歷史的開端,這樣的史觀最早可以追溯到司馬遷(前一四五—前八六)的《史記》。司馬遷是漢代偉大的史家,不過他並沒有使用我們今天看得到的那些考古證據,《史記》影響深遠,首開歷史的線性敘事,將三代和秦、漢連結起來,然而,夏人、商人和周人其實並沒有司馬遷書寫時的那種線性心態。首先,這三個政權從來沒有建立某個大型政治體,並沒有大到能涵蓋所有我們今天叫做「中國」的地域;近數十年的考古發掘則早有顯示,從文明肇建之初,在黃河盆地、長江以及其他地區,曾經有好幾個文化同時並存。此外,「中國」這個名稱或是類似的說法,在當時並沒有當作身分的標記,沒有將三個政權整合在一起,不論是這三個政權或是其他被稱為「夷狄」的政治實體,都沒有明顯劃定的政治疆界,總是彼此交錯相疊。事實上,像甲骨材料也顯示,當時有好幾個群體同時並存;甲骨來自於大型哺乳動物的肩胛骨,或是龜骨的底板,是研究上古中國的主要材料。在甲骨中,至少有八個常見的主要群體存在,商和周不過是其中兩個而已,周人和另一個名為羌的人群組成聯盟,最後打敗了商。
商朝的主導思想是什麼呢?他們相信各路鬼神擁有力量,可以影響諸多人間事物,舉凡莊稼、戰鬥或疾病等等;他們宰牲獻祭、占卜吉凶,輔以音樂、舞蹈,形成繁雜的儀典,尤其他們還會燒灼甲骨形成裂紋,以此探察列祖列宗對各種事物的想法和感受。當時的人認為,這些甲骨記錄了與祖先溝通的對話,而商朝的統治者也因為能通靈、能與保佑他們的神靈交流,因此在神聖秩序中扮演必要的連結。商朝的統治者與祖先的關係是互利共生的,並沒有普世的道德前提支撐,而是出於雙方私利而已;他們認為,祖先只會庇蔭那些願意好好祭祀的子孫。因此,統治者需要超自然力量幫忙,藉由儀式向先祖獻祭,而需要祭品的列祖列宗理應達成某些任務,以回應他們的祭拜。
既然商朝統治者的政治權柄建立在他們與強大祖先溝通的門路之上,這種統治可說是神權政治;雖然這些統治者對於自然和社會環境往往只有低度的掌控,但因為借用了鬼神世界的力量,他們補強了這些不足之處。在周人打敗商朝以前,周王像商王一樣,也會在宗廟中進行複雜的儀式祭拜祖先;然而,在周人得勝之後,他們並不將成功歸諸祖先神力對於自己族系的庇護,而是提出「天命」(Mandate of Heaven)這個新的說法,大意是說:他們之所以能打敗商朝,並不是因為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是因為天——超越一切的權威——希望他們贏得勝利,而天命專屬那些德性完備的君主,當商人的行為有悖德性時,便也失去了天命。天命的說法讓周人能夠在家系這個單一的理由之外,替權力找到合法性;也就是說,他們改變了以神權為本的王權,把政治權柄建立在普世的道德基礎之上。周朝的普世天命觀與另一種觀點相衝突:許多人把天當成神祕的、無常的存在,一如《詩經》所說:「偉大的天如此令人如此敬畏,變換如此迅速!祂既沒有所想,也沒有所圖……就算是無罪之人,也在深淵中一同受苦。」(《詩經.小雅》:「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人之所以發展出天命觀,在於其他的家族並不將周人的權柄視作理所當然,因此周人勢必得將自己的權力轉化,讓其他人也可以接受才行。
結果看來,天命觀的影響既深遠又複雜。雖然王權看似神聖而不可侵犯,國祚有機會能長久綿延,但既然任何君王或朝代都需要維持一定的道德水準,他們權威永遠處在危機當中;以刀劍打天下者,固然可以在勝利之後取得暫時的權勢,但同時批評者也能用天命說來剋制掌權者。例如,天象等自然現象可以用來證成現今掌權者的合理性,有時也可以將視為警訊,說明當下的政權治理不善。從中國思想史的大脈絡來看,天命觀的非凡之處在於它替後繼的朝代設下典範,之後的朝代都宣稱前朝是因為膽敢藐視上天給予的道德命令,因此承受了亡國的苦果;天命觀以這種方式提供一條長時段的敘事軸線,將後繼的朝代串連起來,形成一系列正統中國的征服者系譜。
從西周開始一直到春秋早期,周朝肇建時的政治理想都運行良善:周人的統治者對各地諸侯享有最高的政治權柄,諸侯則任用族人作為公卿大臣,在他們輔佐下實際統治全境。因為諸侯享有宗教權柄、擁有土地,而且可以任命官員,這些因素令公卿大臣聚合,一同接受諸侯的統治。然而到了春秋晚期,土地和官位都日漸受到世家大族把持、代代相傳,也就是說,在土地私有制度逐漸發展之下,就算公卿受到免職,他們持有的土地也不會回到統治者手中,結果地方諸侯的權威便遭到嚴重侵蝕。隨著諸候原本一統的權柄日漸衰弱,不同家族開始競相追逐權力和財富,而當西周的政治秩序日漸瓦解時,天命說的權威也因此動搖,「受教育的菁英群體大多開始相信,倚靠上天或神靈已不足以保障日漸衰敗的社會政治秩序了」。也正是緣於這個脈絡,孔子才要為政治秩序尋找新的基礎,雖然表面來看,上天仍然是超越一切的權威,但因孔子並不相信天會直接介入人類的事務,因此他在人世中找尋其他的根本原則,而他呼應所處時代的方法,便是將目光從「與神靈的溝通」移到「對禮制的遵循」;事實上,春秋時代有好些思想家也開始提出疑問,質疑非人力量對政治而言是否真的有那麼重要。所謂政治秩序參照點由上天移到人世,這種變換如果能代表中國政治思想的開端,是因為祈禱已不再能做為解決人類困境的方法;塵世的政治才能;同理,我們因此能把孔子當成敘述中國政治思想的開端,他清楚地解釋,人類在很多方面其實掌控了自身的命運。
推薦序文
導讀〈從政治思想重訪「中國」的多元面貌〉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的地緣政治以及國際經濟等層面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爭議,中國的概念定義與實質內涵成為人文社會科學學界、乃至當代思想界關鍵的探討課題。究竟「中國」在概念意義上的範圍為何?其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與文化脈絡是否有所延續?抑或是有何發展及差異?對於以上問題,近年來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就自身學科的專業背景提出各自見解進行討論。至於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本《政治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則是從政治思想史的視野切入,以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迭為經,政治體制、秩序建構以及身分認同等議題作緯,藉此探討「中國」在思想意義上的複雜性與多元性。
本書英文原版由英國的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於二○一七年底發行,原題為《中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作者金英敏(Kim, Youngmin)現任韓國首爾大學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思想史、政治史與政治學,尤其在儒學與中韓政治思想史相關議題上用力尤多。作者二○○二年自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期間師從新儒家代表學者杜維明,學位論文題目為「重新定義自我與世界之關係:明中葉新儒學論述研究」(Redefining the self's relation to the world: A study of mid-Ming neo -Confucian discourse),此外作者亦曾在歷史學、政治學以及哲學領域之學術期刊上發表中韓思想史相關議題之論文多篇,如其對明代理學家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的思想曾進行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
根據本書〈導論〉及其英文原名,可以得知作者的寫作動機,曾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蕭公權的經典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啟發。在前人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基礎上,作者試圖在歷史書寫乃至史觀詮釋上,有所發覆。本書以長時段通史維度書寫中國政治思想的同時,亦強調超越國族主義史觀的一元論述。受到十九世紀歐洲國族主義以及實證史學思想的影響,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學界出現了一批中國通史類著作,其中膾炙人口者,諸如錢穆《國史大綱》、張蔭麟《中國史綱》、呂思勉《中國通史》等。這類通史著作,當中傑出者富有宏觀史識,尤貴考察歷史之延續與嬗遞,然而其中一元論的正統敘事,卻也往往容易造成讀者將所謂中國視為單一均質的整體,尤其是將漢文化以及儒家思想視為中國的主要範疇。
然而近年來隨著國際學界對中國研究的推進,尤其是對中國性(Chineseness)多元複雜內涵的揭示,學者們越來越傾向將中國視為一組在地理疆域、乃至文化範疇上持續變化而浮動的概念。更具體地來說,所謂中國的構成,並不只有漢文化,亦包含經由內陸亞洲(Inner Asia)與海洋世界傳入的非漢文明;另一方面,即便就漢文化抑或是儒家思想本身而言,其內部亦具有高度異質性而不可一概而論。是以本書雖以書寫中國政治思想為綱,卻不以目的論式的敘事強調政治思想對於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延續性影響,而更加側重中國政治思想的內在多元性。
本書作者雖強調思想的內在多元,卻並非消極的解構論者。通過歸結中國歷代思想家對政治秩序的理念與論述,本書在〈導論〉及〈結語〉之外,依時序從先秦至晚清分別以八章的篇幅討論:文明禮俗社會(enlightened customary community)、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國家/政府(state)、貴族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y)、形上共和國(metaphysical republic)、獨裁體制(autocracy)、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政治有機體(body politic)以及帝國(empire)等政治概念。綜觀各章篇幅、內容深淺不一,大體而言深入淺出,其主要特長在於綜合以歐美為主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以及問題意識,分析中國歷代政治思想特色及其變遷。作者係研究明代新儒學出身,故本書探討宋明理學與中國政治思想之相關章節較為出色,而其篇幅與論述相對精煉,可資中國思想史的入門者作為參考。作者在關注儒家思想內在理路的同時,亦能留意對外關係對於中國政治思想之深遠影響,尤其是契丹、女真以及蒙古等非漢文化傳統,對宋代以降中國的華夷觀乃至大一統思想的互動。
通過探討中國歷代政治思想之發展與差異,本書批判性地檢視傳統中國的政治話語。不因循前人之說,作者主張所謂大一統的論述,實際上是建構在高度異質的多元因素之上,至於中國專制政體的形塑過程,亦不乏歷史的偶然性,並非是大一統思想必然導致的結果。在這個脈絡之下,就史學的討論概念而言,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與作為身分認同的中華,實際上並不完全重合,甚至有所矛盾,如作者在〈結語〉中列舉朝鮮在面對清朝的外部壓力時,內部以「小中華」自居的特殊認同,便是典型的例子。關於中華認同或者文化中國的多元性,正體現當代中共政權實際上並不等同甚至無法代表文化意義上的中華。當代史學大師余英時(一九三○—二○二一)曾化用德國文學家保羅.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之語稱「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誠哉斯言。
NT$545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