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架日期:2025-0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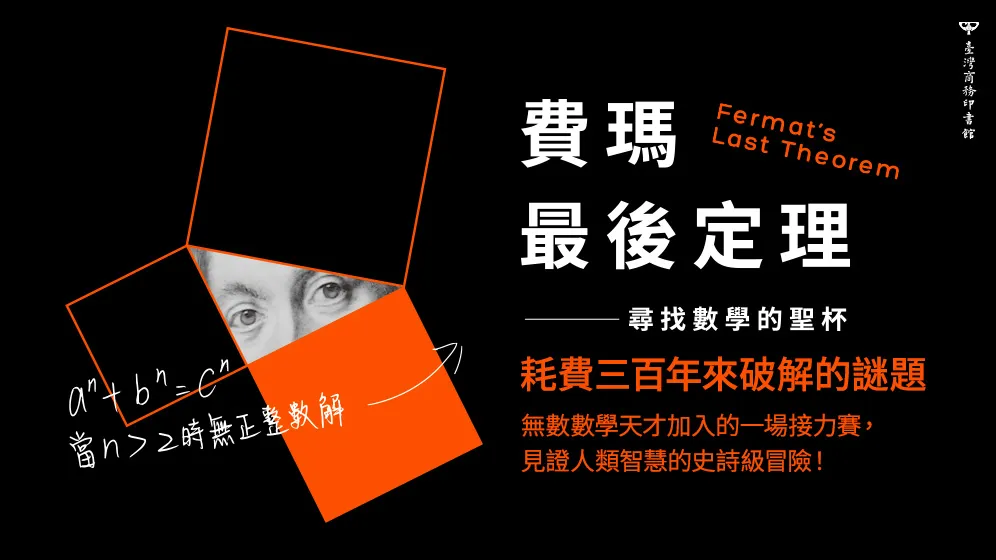
在浩瀚的數學史上,很少有一個命題能夠同時具備這麼多元素:它簡單到小學生都能看懂,卻困難到三百多年無人能證;它串連了古希臘數學的優雅與現代數論的深邃,並最終在二十世紀末化為全世界關注的科學盛事。這,就是《費瑪最後定理》背後的故事——一段足以和任何文學史詩並列的人類精神探險。
賽門‧辛(Simon Singh)並沒有將這本書寫成冷冰冰的數學論文,而是用科學記者的敏銳與故事家的筆法,把數學變成一場高潮迭起的冒險。即使你對數學心存畏懼,也會在翻開書頁後被深深吸引,因為它講述的不只是數字與公式,更是人類面對未知時的勇氣、孤獨與執念。
一條寫在書邊的方程式,引發三百年的追逐
故事的開端,是十七世紀法國的律師兼業餘數學家——皮埃爾‧德‧費瑪。他在閱讀古希臘數學家丟番圖的著作時,隨手在書頁邊緣寫下了一行式子:「an + bn = cn,當 n > 2 時無正整數解」,並補了一句令人抓狂的註解:「我有一個絕妙的證明,但書的空白處太小寫不下。」
就是這行挑釁全世界的文字,成為數學史上最著名的謎團之一。三百多年來,無數天才接力挑戰,從歐拉到高斯,從柯西到索菲亞‧科瓦列夫斯卡婭,沒有一人能將其完全證明。數學界將它稱作「最後定理」,因為它是費瑪眾多命題中最後一個未被證明的命題,也是最難啃的那塊骨頭。
從畢氏定理到橢圓曲線:數學的宇宙航行
本書的精彩之處,在於它讓讀者一步步理解,這條看似簡單的方程式,為什麼如此難以攻破。當 n = 2 時,它就是我們熟知的畢達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邊平方等於兩直角邊平方和,(3, 4, 5) 就是一組經典解。然而,一旦指數變成 3 或更高,數學的世界就像從平原驟然轉入險峰,傳統的計算技巧不再奏效。
賽門‧辛將這段數學演變描繪得像一場太空探索——最終,證明費瑪最後定理的關鍵,不是直接攻擊它,而是建造一艘「太空梭」——谷山–志村猜想(橢圓曲線與模形式之間的神秘對應)。這是數學界中幾乎無人敢想的假設,如同發現兩個原本互不相關的星系竟共享同一組「數學 DNA」。
安德魯‧懷爾斯正是駕駛這艘太空梭的人。他在劍橋求學時第一次遇見費瑪最後定理,十歲的他便立下終生志向。三十年後,他在嚴密保密的情況下獨自鑽研七年,最終於 1994 年在劍橋公佈了證明。這是科學史上少見的浪漫時刻——一個人,對一個看似無解的問題,付出了幾乎全部的生命力。
數學的浪漫:理性與想像力的結合
《費瑪最後定理》的迷人之處,不只在於懷爾斯的偉大勝利,更在於它揭示了數學的雙重面貌——既是冷靜嚴謹的推理,也是充滿激情的創造。數學不只是計算,它是一場智力與美感的遊戲,是對「完美」的永恆追尋。
賽門‧辛用通俗生動的比喻,帶領讀者跨越數論、模形式、橢圓曲線等艱澀領域。你不需要是數學系出身,也能感受到其中的詩意與壯闊——比如他將谷山–志村猜想比作「在街上隨便找一隻貓驗尿,結果成分和某條狗的汗完全一致」,荒誕卻令人過目難忘。
三百年的接力,集體智慧的結晶
這段歷史不是孤立天才的單打獨鬥,而是數學共同體跨越世紀的集體努力。每一位挑戰者,即使最終失敗,也為後人留下了工具與思路。正如本書呈現的,費瑪最後定理的證明之路,其實也是數學發展史的縮影——從古希臘的幾何,到近代的代數,再到現代的抽象結構。
更動人的是,這是一個純粹由好奇心驅動的旅程。費瑪最後定理並沒有直接的實用價值,但它卻像聖杯一樣吸引著一代代數學家。這種為了未知而投入的精神,本身就是人類文明最珍貴的財富。
為什麼今天我們仍需要讀《費瑪最後定理》
在 AI 能瞬間解方程、生成證明的時代,我們或許會懷疑:人類還需要學數學嗎?這本書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數學不只是答案,更是提問與探索的能力。
賴俊儒在新版導讀中提到,真正的數學素養是「面對未知時直面問題的勇氣與行動力」。費瑪最後定理的價值,不只是它被證明了,而是它在三百年間培養出無數數學家的思維品味,讓人們見識到數學世界的深度與美感。
結語:一部人人可讀的數學史詩
《費瑪最後定理》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它將數學還原為一場扣人心弦的人類冒險。它既有謎團的懸疑感,也有人物傳記的溫度,還有知識探險的壯闊視野。無論你是數學愛好者、科學迷,還是只想看一個好故事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驚喜與感動。
讀完之後,你或許會和十歲的懷爾斯一樣,對數學燃起一種難以言喻的熱情。即便不去解什麼定理,你也會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有些追尋本身,就值得一生投入。